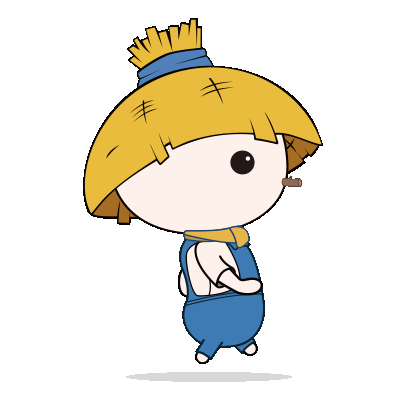她如今, 只肯疏远地叫他镇远侯了。傅霆州看看王言卿,又看看陆珩,依然皱着眉道:“胡闹, 这里关押着朝廷重犯,你知道有多危险吗?”
“我知道。”这回是王言卿接话,她双手交握, 静静立着,说,“这里有点潮, 我待着不舒服。能快点开始吗?”
两个男人一起哑然了, 傅霆州听到她不舒服,刚要说送她出去,陆珩却突然开口,强行压过傅霆州的话:“搬火盆来, 给夫人驱寒。”
陆珩这句夫人像一根无形的刺,扎的傅霆州心脏抽痛, 剩下的话再也无法说出口了。他现在以什么名义护送她呢?她已有夫婿, 他也另娶新人, 于情于理, 傅霆州都该避嫌。
傅霆州沉默,陆珩趁机更改地牢的安排。搬来火盆后,地牢中立刻明亮很多, 阴魂不散的潮气似乎也消退了。王言卿无意陪这两个男人在这里浪费时间,直接问:“伍胜的牢房在哪里?”
陆珩指向最里面的一间, 王言卿压根不等人陪同, 自己举步走了过去。陆珩赶紧追上, 傅霆州也不由跟了过去。
傅霆州脸若寒冰, 压低声音质问陆珩:“你这个夫君是怎么当的,竟然让她来这种地方?”
这句话不知道戳中了陆珩哪里,他也忍着怒,冷冷回道:“镇远侯,我再提醒你一次,如何审问由我说了算。我才是她的夫君,我当然了解她。”
陆珩的话仿佛隐含着很多他不知道的信息,傅霆州讶异,恍神的功夫陆珩已经超过他,快步追到王言卿身边。傅霆州定了定神,决定暂时按兵不动,先跟上去看。
王言卿进入牢房后,一抬眼便看到一个脏污狼藉的男人,他手上、脚上都套着锁链,衣服破破烂烂,有些地方还凝结着黑褐色的血迹。
傅霆州缀在后面进入,他看到伍胜的模样不断皱眉。他时常出入牢房,早已习惯这副景象,甚至伍胜会变成这样,和他脱不了干系。可是,这种血腥肮脏的场面怎么能让王言卿看到呢?
她理应穿着锦衣华服,在温暖的屋子里焚香看书,眼中只有春花秋月、诗词歌赋,一辈子都不会看到这个世界的阴暗。
而不是出现在阴冷的地牢。普通男人见了牢狱场面都会不适,女眷岂不得做噩梦?
傅霆州正要让人搬屏风来,挡住血腥,王言卿已经掀开幕篱,平静地看向这一幕。牢房里的血腥味浓郁的散都散不开,她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
她收起幕篱,很自然地递到旁边。陆珩从容接过,宛如跟班一样帮王言卿拿着东西,安安静静站在旁边。
傅霆州眼角余光扫向陆珩,拿不准他脑子里进了什么水。王言卿朝伍胜走去,礼貌问好:“伍大当家,久仰。”
伍胜掀眼皮瞅了王言卿一眼,依然无精打采靠在墙上,全不将一个女子放在眼里。王言卿对旁边的狱卒说:“我和伍大当家说说话,怎么能让客人带着镣链?把大当家身上的锁打开吧。”
狱卒惊诧,反射性看向门口。陆珩微微点头,傅霆州没动弹。狱卒没办法,只能试着打开伍胜手上的锁,但依然不敢松开他的脚链。
“松开吧。”王言卿说,“伍大当家痛风犯了,即便没有脚链,他也走不了路。”
牢房中的人都是一惊,伍胜霍然抬头,恶狠狠地盯着她:“你们调查我?”
“锦衣卫再神通广大,也无法探知不在大明领土上的人。”王言卿笑道,“大当家脸上的痛意很明显,无需情报,光靠眼睛就能看出来。”
狱卒脸上表情微妙,是这样吗?为什么他们就没看出来?
傅霆州自从进来后眉头就没有松开过,他看向陆珩,不明白他们在玩什么花样。陆珩却微不可见地摇头,示意所有人都不要打扰。
伍胜说了那句话后,又垂下头,一副随便你们怎么说的样子。走廊外面增添了许多火盆,连着牢房里的光线也明亮很多。王言卿看着伍胜,道:“伍大当家在海上漂洋二十余年,留在海外的时间兴许比踩在土地上的时间都长了,竟还会因为我说你不是大明人而生气?”
伍胜原本看他们带一个女子过来的时候,还笑朝廷黔驴技穷,莫非他们打算用美人计?但现在,伍胜知道他们为什么派这个女子了。
妖女,倒确实有些妖邪在身上。
伍胜依然垂着脸,看不出任何表情波动,然而他细微处的肌肉抽动、纹路走向,全部落在王言卿眼里。
王言卿看着他,慢慢说:“大当家和二当家虽是兄弟,性格却截然不同。”
伍胜脸颊上的肉快速抽动了一下,牙肌绷起,很明显在忍耐情绪。王言卿继续道:“我曾见过二当家一面,二当家说的一口好倭语,哪怕说他是倭人,也不会有人怀疑。二当家看起来也比较亲近东洋那边的东西,对大明毫无情感。但大当家却相反。我实在很好奇,大当家把弟弟当儿子一样养大,却眼睁睁看着他忘记祖宗之言,忘记乡音故土,甚至不认可自己身上的血液,大当家看到这些,心里是怎么想的呢?”
&nbs p;伍胜终于忍无可忍,抬起眼皮,戾声骂了句:“滚。”
“大当家不愿意听,我却要告诉你,若不制止倭寇之乱,任由他们霸占沿海,将来,还会有数不清的孩子像二当家一样数典忘祖,恨不得剥去自己的皮成为别人。大当家,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吗?”
伍胜冷哼一声,道:“关我何事?我只不过是无数被海禁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之一,只能离开家乡,挣点钱养活自己罢了。那些皇帝弑兄弑父,却让百姓对他忠义仁孝,狗屁忠孝,莫非能当饭吃吗?”
看得出来伍胜脑子很清醒,有着强大的自我认知,王言卿不和他辩论,换了个方向道:“那沿海那些无辜的老人少女呢,他们做错了什么,要成为你挣钱的牺牲品?”
果然,抛出这个话题后,伍胜就不说话了。对付这种最看重江湖义气的人,就要用老弱妇孺攻心。王言卿说道:“大当家,你自己可能觉得你这一生无愧兄弟朋友,可是,那些没有自保之力的老人、女子,却因为你的义气,和家人再无机会团聚。金台岛已败,你无须再为谁负责了,水战时,有一伙倭人趁乱乘船逃跑,他们去了哪里?”
伍胜紧绷着脸不回答。王言卿仔细盯着他,缓缓道:“昌国县,北麂,南麂……”
王言卿停下,了然地说:“看来他们往南麂去了。他们会带救兵来吗?”
“南麂岛上有哪些人,倭人,西洋人,还是海盗?他兵力如何,比你的人多吗?”
伍胜不想说,但哪怕他一言不发,那个女子也能准确无误读出他的心声,邪门极了。最后,伍胜只能闭住眼睛,控制着自己想其他事情。只要他不听不想,这个女子就没办法。
伍胜强行堵住耳朵,王言卿确实没办法了。这种办法只适合攻其不备,他越意外,脸上的信息才越丰富。时间长了,对方生出防备之心,王言卿就很难获得准确消息了。
不过,有这些信息已经够了。王言卿转身,还没说话,陆珩已经上前,仔细帮她带上幕篱,然后握着她的手取暖:“冷不冷?”
“有点。”
“那我们出去吧。”
陆珩护送王言卿出门,傅霆州也跟着往外走。他路上一言不发,眉宇紧紧皱着,时不时抬头,看着王言卿的背影欲言又止。
等终于走出地牢,王言卿接触到阳光,舒服地叹了口气。
她实在不喜欢地下那股阴郁绝望的环境,仿佛连骨缝都被死气缠绕。王言卿想赶紧回去换衣服,隔着幕篱问:“刚才的话你们都听到了,无需我再复述一遍了吧?”
陆珩说:“今日辛苦你了,我送你回去。”
“等等。”傅霆州突然出声,叫住他们两人。傅霆州眼神复杂,问:“刚才的事情,你们作何解释?”
陆珩回头,凉凉瞥了他一眼:“我夫人的事,为何要和你解释?”
陆珩语气不善,但傅霆州并没有被陆珩的刺逼退,反而咄咄问:“她能察言观色,以致于无需说话就能看懂犯人的想法?”
毕竟是跟在他身边十年的妹妹,傅霆州原来就知道王言卿特别善解人意,有些时候简直和他心有灵犀,无需明说两人就能达成默契。今日他看着她游刃有余地审问伍章,温温柔柔就将纵横海上的海盗头逼到崩溃,傅霆州才突然意识到,或许,不是她和他心有灵犀,而是她能看懂他的想法,故意顺着他说。
傅霆州想到过去那十年,忽然觉得不寒而栗。她一直在迎合他吗?那陈氏和侯府下人对她的排挤,她也一直看在眼里?
她在傅家十年,是不是真的从未开心过?
傅霆州灼灼盯着她,目光穿过幕篱,执着地望着她的眼睛。王言卿隔着层层叠叠的白纱,并不回答。陆珩生气了,他握住王言卿的手腕,将她拉到自己身后,以一种绝对占有的姿势挡住傅霆州:“镇远侯,这是我的夫人,你没有资格逼问她。”
陆珩挡在前面,傅霆州只能看到她随风飘舞的白纱。傅霆州特别想拉住王言卿,掀开她的面纱,好好问个明白,可是他知道他不能,她已经嫁人了,不再是他的妹妹了。
傅霆州只能忍着滴血的心,极力摆出毫无感情的态度:“这是战场,任何一次行动都涉及几万人的性命,不能儿戏,我必须确定情报的对错。”
王言卿一听,轻笑一声:“爱信不信。”
说完,她再不理会那两个男人,转身就走了。
清风拂过,白纱随着风起伏,在阳光下像一阵缥缈柔软的雾。陆珩和傅霆州的目光都跟着那道白色幕篱,但谁都没有动。
在王言卿走出说话范围后,傅霆州问:“你之前几次破案如有神助,就是靠她逼问出实情?”
陆珩听后轻笑:“镇远侯自己是个废物,不要觉得别人都和你一样。我陆珩为人处世,从不需要外力。”
陆珩这个人好好说话大概会不舒服,连自夸都要踩傅霆州一 下,暗讽他借婚姻助力仕途。傅霆州不想再和陆珩纠缠这个话题,他冷冷问:“那你敢说,你没有利用她达成目的吗?”
“我事先明明白白解释给她,她听后愿意参与,有何不可?”陆珩说道,“我们夫妻是志同道合,殊途同归,不像你。别拿你的婚姻情况曲解我们。”
“她从小就不善拒绝人,为了让别人高兴宁愿委屈自己。当真是她自己愿意,而不是顺从你吗?”
“那依你看,今日她的表现,是为了讨好我,还是她自己喜欢?”
傅霆州一时语塞,王言卿今日步步为营、掌控全局的样子,和他记忆中安静的卿卿大有不同。那样明亮的眼睛,坚定的气势,会是为了讨好一个男人吗?
傅霆州沉默了,陆珩觉得他和傅霆州没什么好谈了,道:“她天生细腻敏感,幼年又为了生存不得不察言观色,这才锻炼出远超常人的体察能力。虽然我很心疼她小时候受的罪,但既然她拥有了这种能力,就不该埋没于内宅,用来逢迎婆婆和丈夫。皇帝也知道,默认她掺手一些机密案件,你要是真想让她好,以后就别提她的名字。而且,管住你自己,在公开场合和她保持距离。”
陆珩瞥向他,目光冷锐含锋:“别忘了,你已经成婚了,武定侯的外甥女婿。”
·
王言卿独自走了没多久,后面很快追来一道脚步声。陆珩握她的手,被她躲开,但陆珩不依不饶,坚决捞起她的手,和她十指相扣。王言卿挣不开,闷闷放弃了。
陆珩慢慢说道:“卿卿,你和他生气,总不能迁怒我吧?”
“没有。”
“没有生气,还是没有迁怒我?”
王言卿不说话,陆珩道:“卿卿,我不会怀疑你,只要是你给的消息,我会立刻按你说的做。但是傅霆州这个人小肚鸡肠、刚愎自用、狂妄自大、自以为是……”
陆珩眼睛都不眨地骂傅霆州,大肆公报私仇,王言卿没忍住,轻轻笑了。
她并不是生气自己好心帮忙,别人却不信她。她只是看到傅霆州那么惊讶,心里替自己不值。过往十年,今日他才发现她的不一样,如果王言卿没有坠崖、没有失忆,他是不是一辈子都觉得理所应当?
善解人意,温柔懂事,解语花……呵。
王言卿心情低落,见到陆珩也没法立刻热络起来。但陆珩见缝插针地在她面前挤兑傅霆州,为了贬低傅霆州什么词都敢用,她突然觉得无所谓了。
从前种种,譬如昨日死。现在她的夫君是陆珩,还在乎以前做什么?
王言卿说:“行了,我并没有介意你们怀疑我。他是主帅,所有功过都算在他身上,骤然听到对手的兵力部署,想再确定一下无可厚非。”
她说到一半,感觉陆珩的手指锁紧,夹得她指根都痛了。陆珩意味不明,问:“卿卿,你在替他说话?”
“我没有,说句公道话而已。”
很好,陆珩原本是怕王言卿心里不痛快,现在王言卿没事,他心里倒极其不痛快了!
·
陆珩连着杀了两个高官后,南直隶再没人敢和总督对着干。傅霆州金台岛大捷,像一剂强心针注入众人心中,军队中士气大振,官场上也没人再说丧气话了。
也可能是不敢。有主和意向的官员陆续因为意外离世,众人都不是傻子,看看死掉的那些人,再看看待在南京陪娇妻游山玩水的陆珩,谁还敢唱反调。
陆珩敲山震虎后,官场风气一清。高层没人撑腰,军队也很快安分下来。战场上怕的不是失败,而是军心动摇,傅霆州趁机将原来的队伍打散,重新编队,并且在民间招募善斗的民兵。
别小看平民百姓,江浙多丘陵,有些山村封闭而团结,两村打斗起来可比战场凶狠多了。
职业的打不过领钱的,领钱的打不过天生喜欢的,傅霆州把这些人招募进来,单独编队,对倭战斗力立刻获得极大提升。
之后明军又几次和倭寇交战,实战中涌现出许多出色将领,比如进士出身自学兵法的胡宗宪,出身登州武将家族的戚继光,朱纨的旧部俞大猷、卢镗……
明日,大军即将围攻沿海最大的倭寇头目之一——徐海。如今倭寇大概分两股势力,一个是徐海,一个是汪直,只要能除去这两人,其余不过游兵散勇,不成气候。
如今和倭寇开战已到达攻坚阶段,他们对上的不再是小股零散的海盗,而是真正有组织有纪律的武装势力。若他们能打败徐海,之后全力对付汪直,朝廷的胜算立马加大许多,若明日这一战失败……那徐海和汪直相互配合,拖着他们两线开战,朝廷军疲于奔命,越发难以取胜。
所以,明日这一战至关重要。
开战前夜,王言卿和陆珩出城,登上山坡,眺望广阔无垠的海面。
海面幽蓝神秘,海浪拍打在 岸上,潮声连绵不绝,听着让人心静。王言卿叹道:“真是不愿意想象,明日,这里就会被炮火和尸体染红,再不复此刻的平静美丽。”
陆珩说道:“自然无情,千万年来没有为任何人改变过,不出一日,海洋就会恢复原本模样,回不去的只有人。”
两人站在山岗上,背后是万家灯火,面前是浩瀚海洋。海风从四面八方吹来,掀的两人衣襟猎猎作响。王言卿压住胡乱飞舞的头发,问:“战争会结束吗?”
会吗?陆珩这次没有再给她编织美丽的梦,而是说:“我不知道。”
人的贪欲无穷无尽,只要有利益,就会有争斗。人的贪婪不止,战争就永远不会结束。
陆珩问:“你可知为何会有倭寇?”
“因为东瀛内乱,民不聊生,许多倭人外逃。”
“不是。”
“因为西洋人造出了大船,能远渡重洋来我们沿海,所以有些人被利益驱动,和西洋人做生意?”
“也不是。”陆珩说,“这些最多是外因,倭人一共才多少人,能逃出来多少;海岸线就在这里,不是西洋人也会有其他人,他们不造船,沿海就没有斗争了吗?倭寇最根源的起因,其实是海禁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沿海和内陆不同,这里人口繁多,地不够耕种,自宋以来,浙闽许多人就靠做生意维生。朝廷下令海禁后,他们断了生计,只能各地流窜,悄悄运货,想方设法躲避官兵追捕,逐渐演变成海寇。如果人和地的冲突不解决,即便平定了这一批倭寇,再过几十年,还会发展出新的问题。”
“既然如此,为什么不放开海禁呢?”
陆珩摇头:“治理国家,哪是简单一个选择题就能管好的。前几朝皇帝曾陆续松动海禁,在沿海设市舶司。流窜的倭寇是少了,但又牵扯出侵占土地、官商勾结等问题。皇帝刚登基时,东瀛两个幕府的遣使团在宁波府市舶司相遇,他们互相敌视,大打出手,引发大规模的仇杀,两方人马沿路烧杀抢掳,害死了很多百姓和官兵。这件事情后,皇帝便关闭了浙江、福建的市舶司,拒绝让倭人登陆。官方途径关闭,他们就只能和私人勾结,渐渐演变成倭寇之祸。”
王言卿这段时间在江南,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,她意识到那些飘在海上落草为寇的海盗,未必就是天生坏种。伍胜其实有句话说得对,人都活不下去了,谈何忠孝仁义呢?
王言卿发自真心地问:“那海禁,真的是正确的吗?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陆珩回头,笑着看向她,“这是皇帝该考虑的问题,我怎么知道呢?这么大一个国家,一管就死,一放就乱,史书上那么多英豪都感叹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,我何德何能,可以回答这种问题?”
王言卿脑子里很乱,她想不出答案,默默站在陆珩身边,和他一起看向茫茫海域。
这是一个血腥的时代,党争激烈,战火纷飞,每天都有官员卷入朝堂内斗而亡。但这同样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,朱纨,戚继光,胡宗宪,俞大猷,京城里有皇帝、夏文谨、张敬恭,或许,还应该加上傅霆州和陆珩。
人才辈出,就是盛世的重要标志之一。他们每个都是顶尖的聪明人,齐聚在同一个舞台上,惺惺相惜又自相残杀。她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,亲眼见证了这些天才的风起云涌。
王言卿问陆珩:“倭寇一战影响深远,将来必是史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可是,史书只会写胡宗宪巡抚浙江,巧计擒贼,戚继光、俞大猷保家卫国,英雄名将,其中可能丝毫不会提及你。你不会不甘心吗?”
陆珩失笑:“人生连自己这几十年都活不明白,管身后名声做什么?对锦衣卫指挥使来说,出名可不是什么好事,我巴不得所有人都不要记得我。”
“你真的不在乎吗?”
陆珩望着遥远的海平面,海天一线,灿烂星河像是要倾入海中。天地如此广阔,人何其渺小?
陆珩说:“现在大明繁荣昌盛,百姓安居乐业,就够了。”
有人光芒万丈,名垂千古,就要有人站在黑暗中,负重前行。盛世不只是光鲜亮丽的,更多地方隐藏在泥里,溃烂生蛆,需要有人剔掉里面的腐肉,扛着它继续前行。
但将来大家能记住的,始终是那个辉煌强大的盛世。
海风越来越冷了,再等下去城门要关闭了。陆珩和王言卿相携下山,他们两人的马系在树上吃草,看到他们回来,兴奋地长鸣。
陆珩先解开王言卿的马,将缰绳递给她。王言卿熟练地翻身上马,她坐好后,陆珩也上来了。两人无需再多言,陆珩轻轻喝了一声,骏马立刻展蹄飞奔,王言卿随即跟上。
他们没有叫侍卫,一前一后朝城门奔去。
背后新月如钩,寒风萧萧,前方九重城阙,万家灯火。
而此刻,唯有他们两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