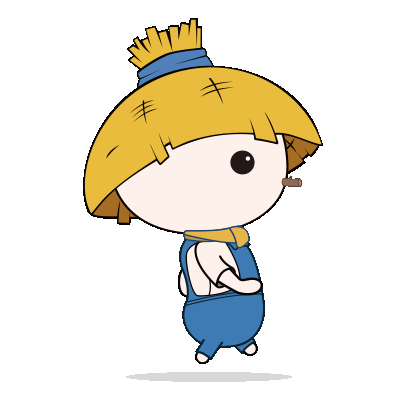苏晏慢慢走过去,问:“何事叫我?”
沈柒说:“无事,就是叫叫”
苏晏觉得这屋里气氛古里古怪,连带摇曳的烛光都暧昧,有点不自在:“既无事,那我便回去了。”
“急什么,你家里是有娇妻美妾,等着回去给你暖床?”沈柒似笑非笑地看他,“还是那两个蠢笨小厮,你不回去,能把他们饿死?”
“那倒不是。因我出门前交代了酉时回去,耽搁太迟徒惹人担心。”
“我这边你耽搁了两天,也不见得顾及到我会担心。怎么,在你心里,我这‘过命兄弟’连小厮都不如?”
苏晏叹口气,坐在床沿哄他:“七郎,你不要说气话,我之前都道过不是了。”
沈柒作勉力抬头状:“我现在动弹不得,说话还得抬头看你,实在吃力,伤口也疼。你躺下陪我说会儿话吧。”
“……我奔波一天,满身汗尘,不好躺床。”
“那就先去沐浴,香汤都备好了,还有更换的衣物,按你的身量新做的,都是你中意的颜色。”
“……”
沈柒见苏晏沉着脸不答话,便又笑道:“都伤成这样了,还怕我非礼你不成?”
苏晏心道:你是个有前科的性侵犯,鬼才信你。又忍不住打量沈柒的伤背,觉得这种状况下,他要真能再做点什么出格的事,那下一步就该羽化登仙了。
沈柒唉声叹气:“我受伤至今,寸步离不得床,又不想被下人看笑话,常整日不说一个字,你再不与我说几句话,我就要哑了。再说,我也想知道北镇抚司情况如何,冯去恶如今是什么下场。你若要清查他的党羽,我还能帮上忙。”
苏晏听他说得有几分可怜,再加上梳理锦衣卫那个烂摊子的确也需要他帮忙,心想陪他聊会儿天也无妨。他要再敢动手动脚,我就拿硬枕头砸他的背。
泡完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,苏晏擦干净头发,换了件居家的月白贴里和长裤。布料用的是上好的七里湖丝,可总觉得有些太透、太薄,水流似的淌在身上,轻若无物,害得他走两步就忍不住低头看,确定自己是穿了衣服的。
沈柒趴在床沿,见苏晏走进内室,人未近前,温润的水汽已携着丝丝缕缕的暗香袭来。这气息仿佛火引,从他的眼耳口鼻渗入,点燃体内储存许久的情欲,一路蔓延向小腹。
光是看到个人影轮廓,他就忍不住亢阳勃发,然而身下抵着床板,并没有任何可供勃发的空间,反而硌得他胀痛不已。
沈柒难耐地挪了挪下半身,牵动后背伤口,脸色一白。
苏晏还以为他要给自己腾空间,忙劝阻道:“七郎不必客气,这里面足够我躺。”
沈柒暗恨:谁要跟你客气!要不是这该死的伤碍事,你这会儿都已经怀了我的种!
苏晏小心地绕过他,爬上床,躺在靠墙的那半边。
拔步床之所以称为拔步床,就是因其床面阔大,可行八步两人并肩绰绰有余,再躺一人也不嫌挤。
苏晏后背一挨到绵软的床褥,四肢百骸就彻底放了松,像个被磕入平底锅的荷包蛋,蛋黄死得其所地荡漾着,只想就这么摊一辈子。疲惫的骨缝发出满足地微响,他呻吟似的长吁了口气。
沈千户翻不了身,恨不得在床板上掏个大洞,解救他无处安放的“好兄弟”。
迫于无奈之下,他只好深呼吸,调节体内真气,努力平息着贲张搏动的血脉。
苏晏将自己摊平后,困意上涌,勉强打起精神,问:“你想和我聊什么?”
什么都不想聊!你是君子动口不动手,我却只想做小人。沈柒咬牙道:“聊聊你今日新官上任,都做了些什么?”
苏晏把今日几处奔波之事,三言两语跟他说了。
“做得不错。经历司储存文书,看似烦牍无谓,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关键之处,冯去恶再怎么小心行事,也总会在累年记录间留下蛛丝马迹。还有你所调的官员档案,如果我没记错,锦衣卫百户以上共计一百六十八人。”
苏晏困得睁不开眼,只脑子还在朦胧运转,依稀记得,的确是大一百多份档案。
“这些人我十有八九都认识,其中一大半,我能说出他们近十年来的行事和风评。”沈柒故意顿了顿,等着他来惊喜讨教。
谁料身旁一片寂静。
沈柒努力撑起头,抬眼瞧去,苏晏半侧向壁里,已沉沉地睡着了。发簪不知何时被他拔掉,兀自捏在指间,一头微湿的青丝犹带水汽,绸缎般散在枕外,衬得脸颊粹白剔透,有如佛经所言,绽放于黑色业火之中的优钵罗花。
这一刻,满手血腥的沈千户愿意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,甚至向漫天神佛许愿,愿意倾其所有,只为让枕边这个少年永远留在他的生命中。
他慢慢抬手,一点点抚摸苏晏的脸,暗哑地、轻声地唤道:“娘子。”
-
苏晏在满室晨光中转醒,仰望帐了句:“清理锦衣卫并非易事,若有疑难之处,不妨来问我。待我能动弹了,就去北镇抚司帮你。”
苏晏安抚道:“放心,我做得来。你就安心在家养伤,当个运筹帷幄的军师即可。”
沈柒失笑:“我这种没读过几本四书五经的,能当军师?”
苏晏调侃:“你这种满肚子坏水的,还能当义士呢!”
沈柒忍笑忍得伤口疼,苏晏惊觉耽搁太久,这都巳时快过午了,赶紧出门坐马车。
在沈府大门口,他刚踩上车凳子,又来了变故。一名白发长须的清癯老者,带着个侍童,拦住了他的去路。
“大人请留步。敢问可是大理寺左少卿苏大人?”
苏晏见这老人虽年逾古稀,却眼神明亮、精气完足,颇有几分道骨仙风,不像寻常人,便收回腿,朝他拱了拱手:“正是本官。老人家叫我何事?”
“�,当不得当不得。”老人连忙躬身行礼,“大人是官,老朽是民,哪有当官的给百姓行礼的。”
苏晏态度谦和:“皇爷为宣扬尊老,提倡践行孝德,尚且年年举办千叟宴。本官年未弱冠,对老人家行个礼,又有何难?”
老人抚须笑道:“京城近日,人多称赞苏大人智勇兼全、嫉恶如仇,虽年少却胸怀大仁大义,如今一看,果然如是!”
苏晏被夸得脸红,连连说过誉了,又问找他有何事。
“老朽陈实毓,是一名外科郎中。这些日子沈千户的伤,便是请老朽来医治的。”
苏晏听他名字,隐隐有些耳熟,仿佛是某个著名的医家,一时想不起来。又把“外科”这个颇为现代的词反复咀嚼了几遍,恍然大悟,失声道:“您是著《外科本义》一书的应虚先生?”
这位可是大佬啊!
著名外科学家,自幼精研外科医术,所著《外科本义》被称为“列症最详,论治最精”的外科医学著作,代表了铭代以前我国外科学的最高成就。
陈实毓见他竟然识得自己,意外又欣慰,将来意娓娓道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