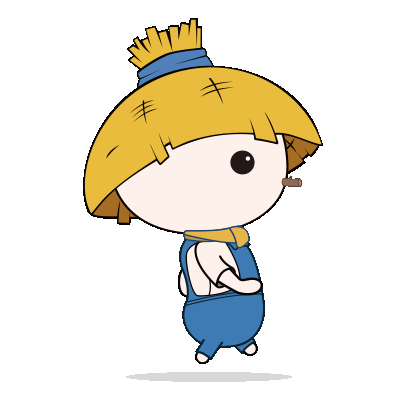我越来越觉得不正常了,几乎是跑着来到了Asa跟前。
Asa问:“你去哪儿了?”
我说:“前面有几个小孩,他们在玩木头人……”
Asa说:“这附近都没有人家,哪来的小孩?”
我带着他一起朝前走去,那三个小孩竟然不见了。他们恢复常态之后,就算不笑也该大声说话吧?但我什么都没有听见,他们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不见了。
有鬼。
不是心里有鬼,是真的有鬼。
我愣在了原地,越想越糊涂。
Asa问我:“在哪儿呢?”
我说:“刚才明明就在这儿啊。”
Asa说:“你拍照片了吗?”
他说:“我哪能想到他们说没就没了啊。”
接着我四下看了看,身上突然掠过了一阵凉意——不但那三个小孩不见了,我刚刚看到的那个砖窑也不见了!!!
这如果是一部漫画,上文那三个叹号应该正好画在我脑袋上。
Asa发现我的表情不对劲,低声说:“你到底怎么了?”
我说:“我可能……出现幻觉了。”
Asa想了想,突然说:“我相信你。”
我看了看他,竟然有些感动,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原来如此重要。
他接着说:“我从来不迷信,你知道的,但是自从我从耳机里听到了多年前的广播,我改变了。”
我说:“我靠,我们来到404之后是不是获得了什么超能力啊?比如千里眼和顺风耳,舒克和贝塔,海尔哥哥和海尔弟弟……”
Asa小声嘀咕了一句:“我不喜欢。”
我说:“你不喜欢什么?”
他说:“超能力啊。”
我说:“我喜欢!我希望这种超能力能帮我找到一卡车的‘错’,赶紧把我妈解救出来。”
Asa说:“你别忘了,凡事都有利有弊。”
说着,他拿过我的望远镜,朝城区的方向看了看,又转身朝哨卡方向看了看,突然说:“有人来了!”
我立刻转过身去。
实际上根本不用望远镜,这个人离我们只有几百米远,是个女孩,穿着一件酱红色皮夹克,很醒目。我说:“那不是四爷吗?”
Asa说:“她是怎么进来的啊?”
我说:“说不定用了美人计。”
很快,四爷就走过来了,我朝她使劲挥起手来,四爷加快了脚步。
她走近之后,我劈头就问:“你怎么不回我信息?”
四爷停下来,做了个哭脸:“我手机摔了。”
我说:“怎么摔的?”
四爷说:“怎么着,你还给以旧换新?”
Asa问道:“你是怎么进来的?”
四爷说:“我找着那个送货司机了。你们是怎么进来的?”
我和Asa互相看了一眼,难道有两个送货司机?
我说:“我们就是坐那辆送物资的车进来的啊。”
四爷的眼珠转了转,说:“你们那辆车是不是翻了?”
我说:“你怎么知道?”
四爷说:“我那个司机说的,所以上头又紧急加派了一车物资。”接着她四下看了看,问我们:“你们现在要去哪儿?”
我说:“办公大楼。”
四爷说:“噢,那我们不同路。”
我说:“你去哪儿?”
她说:“我是来发财的。”
我突然问道:“你来找‘错’?”
四爷略显惊讶:“你怎么知道?”
Asa正要说话,被我打断了,我说:“网上都传开了,很多人都知道。”
她说:“你们也是来找‘错’的?”
我赶紧摇了摇头:“不,我们来找个人。”
她朝前看了看,然后说:“怎么都得进城,既然又遇到了,那就一起走吧。”
说完她就朝前走了。
我和Asa对视了一下,然后我追上去,问:“你知道哪里有‘错’吗?”
她扭头看了我一眼,露出了狡猾的笑容:“不知道,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。”
我说:“没关系,反正我们要找的人也不叫‘错’。”
路上的坑比行李箱的轮子还大,走起来很艰难。
我说:“我帮你提着吧。”
她一点都不客气:“你行吗?”
我伸手提了提,这箱子比我想象的沉多了,提起来竟然有点费劲。
四爷推了我一把,说:“你这小身板还不如我呢。”
然后,她收起拖拉杆,把行李箱提起来,横着一拎,扭着小蛮腰就朝前走了。
Asa看了看我,似乎在说:你再问问。
于是我又快步跟了上去:“四爷,你从哪儿得到的信息啊?”
四爷说:“什么信息?”
我说:“‘错’。”
她说:“这叫商业机密。”
我想试探一下她,于是说:“听说那种东西在垃圾场下面,需要推土机。”
她马上停下来:“真的?”
我说:“网上这么说。”
她四下看了看:“那你知道这里的垃圾场在哪儿吗?”
看来,她也是毫无线索,瞎猫找死耗子而已,我就随口说了句:“跟着苍蝇肯定能找到。”
时间刚刚滑到午后,天色突然变得昏暗,好像太阳马上就要掉进平原尽头了。我们终于终于接近了城区,芦苇渐渐向远处退开,露出了越来越多的地面。
我觉得404就像一本书,最开始的时候,作者做足了功课,娓娓道来,把道路、植物和远处的楼房都刻画得非常细致,突然他发现要截稿了,时间不够了,于是把“白天”一笔带过,把路程也毫不负责地缩短了……就像按了快进键。
我们来到城区边缘的时候,云层越来越厚,太阳完全被挡住了,只剩下一点微光透过云层照射过来,四周的景色暗了几个色格。
我怀疑四爷平时健身,她的速度比我和Asa还快,每次拉开一段距离,她再原地停下等我们。
我问Asa:“你有没有觉得太阳突然就落山了?”
Asa抬头看了看:“就是阴了。”
果然,空气变得非常闷,这是大暴雨的前兆。
水泥路两旁出现了两根石头柱子,很像圆明园遗址,我猜它过去很可能是个象征性的城门,就像荒地和城区的分割线,人类与自然各占半边天。
我们三个跨过去,终于走进了城区。
所谓城区,其实更像一片等待拆迁的住宅区,到处都是废弃的楼房,大都是四五层高的,也有很多低矮的平房,七扭八歪地竖着很多“卌”字形的电视天线。东北的平房顶部不是双坡,也不是单坡,而是平的,上面铺着碱土,那是防水的,长着高高的羊草,甚至还点缀着一些野花,就像一座座屋顶花园。路边偶尔有一些垃圾,时刻提醒着我们,这里曾是人类生活过的地方,但那些垃圾并没有臭味,经过20多年的时间,该腐坏的早都腐坏了,该烂掉的早都烂掉了,该风干的早都风干了。
“城门”旁边有一座尖顶的房子,就像一颗很小的脑袋戴着一个巨大的斗笠,门口有一棵苹果树,它顽强地生长着,开着很多粉白色的花,那些花大得吓人。
前苏联事故核电站切尔诺贝利最近开放了旅游线路,那里的植物也出奇地茂盛,几乎完全覆盖了建筑物。水塘里的鲶鱼,一口就能吞掉一个完整的面包……那是辐射造成的变异。
Asa赶紧从包里找出伦琴仪操作起来,这东西的后壳像老式大哥大,键盘像简陋的老年机,显示屏像交警的酒精检测仪,使用起来又像测电笔。Asa举起它对着空气按了一下,很快它就发出“哔”的一声,显示出了绿色的数字——辐射剂量只有0.1微西弗,而我们使用的电脑显示器的辐射剂量是1.0微西弗。
这里比外面的城市还安全。
我也从包里掏出伦琴仪看了看,发现我的比Asa的少了三个按钮,只有一个开关键。
我说:“你在我的装备上偷工减料了。”
Asa说:“胡说,你这款是傻瓜式的,用起来更便捷。你只要按下开机键,它就处于待机状态了,如果辐射超标,它马上就会报警。”
我说:“等进了404腹地再打开吧,省点电。”
Asa说:“不用,它的电量可以维持7天。”
我试着按下了开机键,黑色的屏幕马上亮起来,变成了绿色。屏幕右上角显示着电量:99%,右下角还贴心地显示着温度:17.6℃。
Asa凑过来看了看,颇为不满:“我跟商家叮嘱过好几遍,要他们把电充满……唉。”
这顾客也是够矫情的。
四爷斜了一眼我和Asa手上的伦琴仪,嘀咕了一句:“这么惜命那就不要来404啊。”
我说:“你没带?”
四爷摊了摊手。
我说:“我把我的给你吧。”
四爷说:“我才不要。万一它响了怎么办?多闹心啊。”
我想起了一个笑话——杀毒软件一直提醒我电脑中毒了怎么办?答:把杀毒软件卸了。
四爷朝四下看了看:“我要去找垃圾场了。”
我赶紧说:“那都是网上的说法,不可信。”
四爷说:“我随便转转,找不着就出去了。”
我有点担忧她:“要不……你跟我们去办公大楼吧。”
四爷说:“去那里干吗?”
我说:“可以跟留守人员问问,哪里有你要找的那种东西。”
四爷笑了:“你敲开一户人家,问,你家把值钱的东西都藏在哪儿了,人家会告诉你?”
想想也是。
我又说:“可是天都快黑了,你一个女孩能行吗?”
四爷露出了一丝不屑:“你们两个大男人能行吗?”然后拖着行李箱就离开了。
我看了看Asa,他只是耸了耸肩,毫不怜香惜玉。
四爷拐个弯儿,不见了。
我对Asa说:“咱们歇会儿吧。”
他说:“好的。”
接着,我们打开手摇式手电筒,走向了旁边那座尖顶的房子。
木门虚掩着,我轻轻推开它,走了进去。地上的灰尘很厚,它们可能很多年都没看到过人了,见到我们立即升腾起来,我赶紧捂住了鼻子。
室内的举架很高,摆放着一排排椅子,尽头有个讲台,上面插着几根蜡烛,它旁边有个小门,上面写着“告解室”,它背后的墙上挂着一个木制十字架。
我用手电筒照了照窗户,它又长又窄,镶着彩色玻璃,大部分都没碎。
这里是个教堂。
我来到讲台前,上面有个本子。强劲的风吹进来,纸页被翻动,就像有人在快速浏览。
我拿起来看了看,这是一本发黄的花名册,首页上写着一个名字——邢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