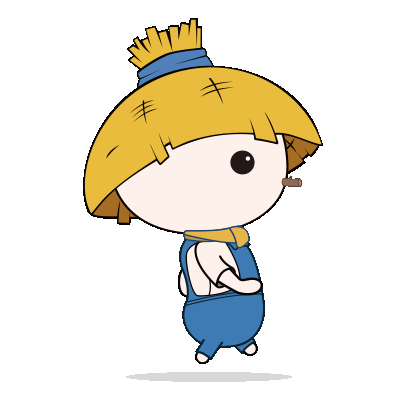东南沿海,一场极不寻常的狂风暴雨过境之后,几十年的大树被连根拔起,许多房屋倒塌。
为了尽快结束流离失所的惨状,霍潇带领士兵们给老百姓修建新屋。
然而,几天后又有官员家眷在上香途中被倭寇杀害。
官兵们对此焦头烂额。百姓们一边瑟瑟发抖,一边幸灾乐祸。
流离失所的穷人们议论道:“世道果然是公平的,不能总是让穷人受苦受难,富贵的人也免不了被杀!”
朝廷因此下旨申饬护国公霍潇,指责他抗倭不力,倭寇屡次杀害官僚家眷,有损朝廷威信。责令他一年内彻底平息倭寇之乱,否则严惩不贷。
霍潇的左副将感到愤愤不平,道:“国公爷来之前,倭寇每日杀害数十个平民百姓,国公爷来之后,倭寇再不敢那么嚣张。但是在朝廷眼里,一个官僚家眷的命胜过一百个普通百姓的命!唉!气人!”
右副将握紧拳头,重重地捶膝,道:“倭寇每次杀害官僚家眷之前,都是偷偷潜入,乔装打扮,然后中途埋伏!这显然是有内奸给倭寇通风报信,故意让倭寇对官僚家眷下死手!可恨!”
“内奸不除,别说一年,就算十年也别想彻底平息倭寇之乱!”
“国公爷有何打算?”
霍潇坐在太师椅上,右手撑着额头,眉头微蹙,道:“没有新的打算。”
除倭寇,除内奸,这是他和士兵们一直在做的事,从未懈怠过。
左副将道:“可是……朝廷既然下旨申饬,咱们是不是应该做做样子……堵住那些文官的嘴?”
霍潇有点似笑非笑,问:“做什么样子?”
左副将道:“多抓几个内奸,杀鸡儆猴!”
霍潇道:“如果证据确凿,咱们何时饶过内奸?如果没有确凿证据,岂能随便扣有罪的帽子?”
“唉!”左副将叹气,低下头。
他心想:如果换作先前的杨铎将军,肯定抓几个百姓当替罪羊,趁机向朝廷邀功。国公爷的正直令人倾佩,但是如果朝廷真的怪罪下来,该怎么办?
轻则降职,重则丢官,甚至下狱。
国公爷有爵位护身,自然不怕,但是自己不像国公爷那样底子厚。
左副将又犹豫着说道:“有几个富商很有做内奸的嫌疑……”
霍潇果决道:“有嫌疑,那就派人监视他们。捉奸拿双,捉贼拿赃。”
左副将道:“末将明白了。”
霍潇起身道:“传令下去,加强巡逻,不可懈怠!”
“是!”左右副将齐声答应,立马去照办。
霍潇注视左副将的后脑勺,眼神意味深长,然后低声对自己的亲卫吩咐几句。
几天后,左副将抓了几个富商,送到霍潇面前,道:“国公爷,这几个是内奸!末将有证据!”
“冤枉啊!小民冤枉啊!国公爷饶命!饶命!”被抓的人哭着喊冤,瑟瑟发抖。
按本朝律法,内奸其罪当诛,内奸的家属全部流放,家财全部充公!
霍潇一直不明白,律法如此严厉,内奸为何还要冒着全家遭殃的危险去勾结倭寇?大部分内奸本身就已经很富有了,却仍然铤而走险。
霍潇问:“证据何在?”
左副将道:“有人证,亲眼见到这几人的家丁给倭寇通风报信。末将已将人证带到。”
霍潇眼神锐利,轻扫一眼证人。那证人立马低头发抖。
所谓人证,就是凭一张嘴,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
如果只说真话,内心光明坦荡,何须做出心虚的模样?
霍潇朗声道:“左副将,你告诉他们,按照本朝律法,内奸有何下场?诬告,又有何下场?”
左副将道:“内奸,其罪当诛!抄家!家眷流放三千里!”
“诬告陷害,打板子三十,再酌情发落。”
霍潇看向左副将,意味深长地道:“诬告的罪罚可真轻!”
左副将低头看地,不敢与霍潇对视。
霍潇扬眉道:“勾结倭寇的内奸,归我管!诬告,归衙门管!别怪我没提醒你们,衙门审案不止打板子那么简单,严刑拷打的严刑至少有七十二种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”
那个证人眼巴巴地望着霍潇,立马张嘴,欲言又止。
那几个痛哭流涕的“内奸”继续不停喊冤。
左副将继续低头看地,身体微微僵硬。
霍潇让左副将出去监督士兵操练,让右副将把几个内奸嫌疑人带下去看押,然后自己亲自询问证人。
这个证人心虚得厉害,再加上对霍潇的战功有几分崇拜,于是不需要审,就交代了实情。他是被左副将要挟,不得不诬告那几个富商,其实他并没有亲眼见到富商的家丁勾结倭寇。
霍潇问:“他以什么要挟你?”
证人心虚地道:“赌债。”
霍潇早已派人在暗中监视左副将,所以在面对证人的反水后,没有丝毫惊讶。
过了一会儿,霍潇让证人去隔壁等着,让左副将进来。
左副将有几分急躁,立马说道:“国公爷是否审问完了?何时把抓获内奸的事上报朝廷?何时处决内奸?”
霍潇背着双手,好整以暇,道:“内奸可恨!抓无辜百姓当替罪羊的人同样可恨!”
左副将面红耳赤,捏着拳头,低头看地,心脏剧烈颤动,答道:“国公爷说得对,确实可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