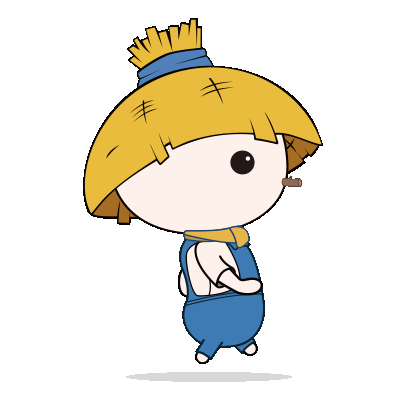1978年,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.38%,每200人中拥有话机还不到一部,差不多比漂亮国落后75年。
这也就难怪改革开放之后,许多人悲观的认为,我们落后到将被开除“球”籍。
《京城文艺》的招待所,还没寒碜到要用“摇把子”电话。
江弦不大娴熟的拿起话筒,扣在耳朵上,“喂,哪位?”
稍等了一会儿,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。
“是江老师么?打扰你了,我是北影厂的施文新呐。”
“施老师,你怎么给我打电话了。”
“您最近有空么?”施文新不好意思道:“我们创作过程中,对小说有几处理解不够透彻,又怕弄错方向,您方便来指教下吗。”
“.”
怎么那么麻烦。
他就一写小说的懂什么《棋王》呐。
再说了,后世这些问题不都是问资方大佬的意思么?
“施老师,电话里说可以不。”
“一句两句恐怕说不清,我是想请你过来,给大伙开个会,也用不了多长时间.”
“行吧。”
江弦还是答应下来,原因有三:
一是为了刷好感度,将来好持续性薅北影厂羊毛。
二是人家施文新那么大岁数、那么大咖位,一口一个“老师”的称呼,实在不好意思拒绝。
三是收音机他收都收了。
“施老师,我明儿一早就过去。”
“哎,伱来了通知我一声,完事儿我领着你在北影厂里转转。”
“好的,再联系。”
“再见。”
挂断电话,江弦顺手从收发室桌子上取了份当天的《光明x报》和《人民x报》。
《人民x报》发了一篇社论《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》。
[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,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!
得寸进尺,继续恣意妄为,必将受到应得的惩罚。
我们把话说在前面,勿谓言之不预。]
看着这篇社论,江弦忽想起黑格尔那句名言:
人类从历史中学到唯一的教训,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。
捏着报纸,推开305房间门,恰巧对上张洁恍惚的眼睛。
“小江,这篇稿子,是你的下一部小说么?”
江弦一拍脑门。
光顾着去接电话,忘记这茬了。
“张老师,你看到了?”
张洁不好意思的笑笑,“对不起啊小江,我还以为是座谈会材料,看了一会才反应过来,但还是没忍住,全看完了。”
江弦尚未写下多少内容,拢共才七八百字,张洁只花了三四分钟便浏览完毕。
阴差阳错之下,张洁成了《动物凶猛》的第一个读者。
江弦也有些好奇自己的修改是否突兀,期待的看向她。
“你觉得如何?”
“故事尚未展开,我不好点评,但这种语言太独特了!”
张洁露出兴奋之色,“我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子写小说!”
江弦搬出一套早想好的说辞。
“我也是想尝试一种新的文体写作,黄遵宪曾经提出过‘我手写我口’的文学主张,我想在《棋王》之后,更近一步的尝试,用白话俚语,将小说对白尽量变通俗易懂。”
“我手写我口?还真是,你真的把京腔口语融入进这本小说里了。”张洁捂嘴笑笑,“而且”“而且什么?”
“我说了你可不准跟我生气。”
“张老师,您尽管指教。”
“你看这里。”张洁指向稿子开头某处。
[在我返城以后,我过上了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。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。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,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,不论人们喜爱还是憎恶都正中下怀。
如果说开初还多少是个自然的形象,那么在最终确立它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。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作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,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,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.]
“你这些句子,就好像一个喝醉的人,说话断断续续,前言不搭后语,动作疯疯癫癫.”
张洁顿了顿。
江弦等待着一个“但是”。
“但又能从中感受到那种无奈和伤感。”
张洁分析一通,露出肯定的笑容,“我太喜欢这样的语句了,这种风格我想不到、也写不出。
小江,我好嫉妒你的才华!”
面对这份褒奖,江弦没再自谦,此时过分谦虚便会显得虚伪。
干脆打趣道:“张老师,你这岂不是说,我这篇稿子字里行间全是喝醉酒的痞气儿。”
张洁被逗笑,“小江,我太确信这篇稿子就是你写的了,你说话真和你的稿子一个味儿。”
“有痞气儿也无所谓,刘鑫武说我是痞子作家,初来我还挺生气,后来想想,至少他还承认我是作家。我写这篇稿子,也想回应一下刘老师对我的期待。其实痞子搞文学这事儿一点都不可怕,可怕的是该去搞政论的人跑来写小说。”
张洁嘴角都合不拢,“你这话能把他气病喽。”
江弦嘴角微扬。
中国的文坛不大,妙人不少。
最妙之人必有刘鑫武老师。
一日,刘老师梦见自己会作诗了,只作出一句,沉博绝丽,还没想出第二句,就狂笑而醒,醒后又惊又喜,不敢相信自己竟有如此功力,匆忙提笔记录下“梦中偶得”的佳句:江湖夜雨十年灯。
怎奈千年前,有个名为黄庭坚的不识趣家伙,夺人之美,在宋朝就写了一句: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。
一时间舆论哗然,刘老师却勇者无惧,解释说:“他的那句是下联,我这句却是上联,下联如何,还要再等巧梦。”
这一等,便让文坛苦等几十年。刘老师也不写小说了,转而跑去祸害《红楼》。
“写稿子、写稿子。”
江弦重新在桌对面坐下,提笔续写《动物凶猛》,不时请教。
“张老师,这样子会不会有些突兀?”
“不会,读起来真实鲜活,热气腾腾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
张洁蒙头修改了会儿梗概,又抬起头瞥一眼桌对面奋笔疾书的年轻人。
欻欻欻~
好几行就写完了。
对这样的创作效率,张洁极为羡慕。
她的写作像挤牙膏般困难。
反观江弦,几乎文不加点,笔翰如流。
当真是无数倍于她的资质。
夜匆匆过去。
翌日,江弦早早爬起。
在食堂吃过早饭,蹬二八车往海淀北影厂骑。
约莫半个小时才骑到附近。
还没停下车子,便瞥见一抹熟悉的身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