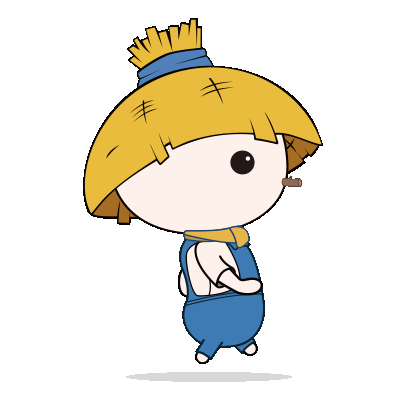别看甘采儿在朱小筱面前信心满满,但其实,她心里很虚。
虽说前世她见过不少风浪,踩过不少坑,但经历过,并不代表能从容应对。
毕竟,前世她与京都那一众世家女子交手,她就没赢过。所有交手都是以她一败涂地,灰头土脸为结局。
以至于到了最后,她名誉全无,只落得个声名狼藉。
若论动手,那甘采儿比她们强上不止十倍,可若论耍心眼,使手段......甘采儿完败。
她不敢托大,觉得这事儿还是要尽早告诉兰亭舟知道,让他小心。
特别是吴馨那一句“吴家与甘家,孰轻孰重,我想他应该知道。如果,他实在是不知,那我就不妨让他知道。”
让她深感不安。
甘采儿脾气急,心里兜不住事儿,一想到什么,立马就去做。茶话会结束后,朱小筱回了兰家小院,而她坐着马车,直接去了鹿鸣书院。
院试定在明年二月。只有通过院试得了秀才功名,才算正式踏上科举之路。因而,所有学子对院试都格外重视,兰亭舟亦然。
为了备考,他最近一直都住在书院里,鲜少回家。平时缺什么或者需要什么,都是遣墨砚和墨云回家来取。
甘采儿已经很久与他没见过面了。
鹿鸣书院管理严格,非师生不得出入书院。所有来探访的家眷,只能经通传后,在书院入口的会客庭院中暂短相见。
兰亭舟听说谢家有人来书院寻他,十分意外。
谢家本家远在陈郡,离旦州八百多里。自从兰家出事后,他们彼此间连通信都少了,更何况是见面。
兰亭舟以为谢家出了什么事,匆忙赶来相见。结果一看,来人竟是甘采儿,不由气结。
甘采儿之前曾假借过谢彩云的名头。所以,这是演上瘾了?
“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?”兰亭舟眉心微蹙,语带不悦。
“哦,我从吴府直接过来的,还没来得及卸妆。为免多事,就延用了谢家表妹的名头。”甘采儿解释道。
“吴府?”
“嗯,就是吴总兵府上。今日吴馨邀请小筱去她茶话会,我跟着去了。”
兰亭舟的眉头蹙得更紧。她巴巴的赶来见他一面,就为给自己讲她去了茶话会?是又发现了什么?
果然,甘采儿紧接着便将在吴府内听到的,看到的,悉数讲给他听。
兰亭舟的脸色一下凝重起来。
他不在意吴馨对他的赞誉,更不在意她口中满含威胁的“要让他知道”。他只是敏锐地捕捉到了“摄政王”三个字。
“吴总兵想将女儿送给摄政王?”
甘采儿一懵,这是她要说的重点吗?她点点头。
“嗯,吴馨是这么说的。”
兰亭舟摩挲着尾指,垂眸沉思了片刻,而后道:“我知道了,你回去吧。”
看兰亭舟一脸若无其事,波澜不惊的模样,甘采儿一下子就急了:“什么叫你就知道了?”
“你知道吴馨拿了什么药?你知道她哪天要往你身上使?你又打算怎么避?”
甘采儿越说越急。
兰亭舟静了半晌,才缓缓道:“不是谁都能给我下药的。”
甘采儿一噎,突然想到什么,脸色瞬间爆红。
“那,那我也是成亲后,才才,才给你.....”
兰亭舟睇了她一眼,轻声叹气:“好了,你放心吧,我心里有数。”
可甘采儿如何能放心!
在她心目中,兰亭舟从来都是正人君子,行事坦荡,风骨高洁,最不屑蝇营狗苟。可越是这样,越容易被心怀叵测的小人算计。
最关键的是,兰亭舟耳根子还很软。每次自己惹他生气,通常只要多求几句,撒个娇,耍耍赖,他也很快就原谅了。
如若他不是这样的人,自己又怎能把他算计到手?吴馨的手段,只会比她更高明,而且吴馨还长得娇娇柔柔,温婉可人,是兰亭舟喜欢的样子,若撒起娇来,估计也比她厉害。
所以,她哪里放心得下。
更何况,还有前世那么大一桩诬告案放在那里。还不知这一世对方又要整什么幺蛾子。
“近期你可要千万小心,绝不能吃外人给的吃食。”
甘采儿眼里的担忧都快化为实质,兰亭舟心里微微一暖,但也很无奈。
“我都听夫人的。今后的饭食茶水,我只吃墨砚、墨云准备的,其余的一概不碰。这下,你可放心了。”
“嗯。”甘采儿虽点着头,可还是一脸忧心忡忡。
兰亭舟不欲她再多想,便岔开话题。
“今日我差点都没认出你来。小红上哪儿学了这门手艺?”
“真的吗?连你都没认出来?”甘采儿欣喜。
“这可不是小红弄的,是我自己亲手化的妆。”甘采儿翘着嘴角,喜滋滋地道。
“你自己?”兰亭舟狐疑地看着她。
“我跟着一个很厉害的师傅学来的。”
于是,甘采儿将去赵姨娘那里拜师的事,一五一十讲给兰亭舟听。
“我记得你曾说过赵姨娘是一个歌伎?”兰亭舟问。
“是呀。赵姨娘是杜大人还在京都时,一个富商送给他的。”甘采儿回道。
“一个歌伎的嬷嬷,怎么会上乘的易容术?”兰亭舟眉头微皱。
“易容术?黄嬷嬷教我的是易容术?!”甘采儿大吃一惊,她使劲搓了搓脸颊,“我这也没易容呀。”
兰亭舟看了她一眼,淡声道:“初级易容术,在皮;中等易容术,在骨。前者会改头换脸或使用面具,后者则会缩骨变形,改变形体。”
“而最上乘的易术容,不动皮肉,不改筋骨,只通过混淆旁人视线,来改变他们看到的容貌。不伤筋动骨,也能达到即使是旧故好友,相逢却不相识。”
“你是说,黄嬷嬷教我的,就是那最上乘易术容?”甘采儿摸着自己脸,犹自不信。
“不过,黄嬷嬷不是赵姨娘的人。”甘采儿忽想起自己打听到的消息。
之前几次与赵娇儿见面,甘采儿总觉得黄嬷嬷与赵娇儿在一起有些违和,便闲时好奇地问过。
“杜恪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,杜大人一气之下罚了当时照顾杜恪的下人,然后就派了黄嬷嬷来照顾赵姨娘母子。”
“我听赵姨娘说,黄嬷嬷是杜家的老人,行事特别周到妥贴。自黄嬷嬷来了后,赵姨娘日子好过了许多。”
兰亭舟眉心一沉,这便更不对了。
赵姨娘歌伎出身,顶多是贱妾。若不是生下儿子,她怕是连妾都当不上。
杜仲子嗣众多,不算女儿,就儿子都有十来个。
如此多子多福的一个大家庭,他怎么会派自家老仆亲去照顾一个妾和妾生子?
而且有此等绝学之人,又怎么只是一个普通嬷嬷?
兰亭舟这时想起陆青宁离开时,给他讲起的另一桩事来。
卢昱在旦州逗留了一个多月才离开。在这期间,他一直住在杜府,闲暇时也会指导一下府上的孩子。其中有两个最得他喜爱,还收作了弟子。临走时,他嘱咐他们,一到七岁就可去京都找他。
要是兰亭舟没记错,那两个孩子其中之一,就有赵姨娘的儿子,杜恪。
卢昱是何等人?他现在头上挂着帝师的名号,不知有多少人削尖脑袋挤破头,也想拜在他门下,可他一人没收。
卢昱其人,一生醉心于书画,几乎不问世事。这次他能出来巡视,就已经很奇怪,然而更奇怪的是,他居然主动收当地官员的孩子当学生。
这极不符合他一贯的作风。
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,碰巧的事多了,那就是刻意为之。
看来,旦州虽地处偏远,远离朝堂,却似乎并不简单。
吴家与摄政王有牵连,而杜府的问题好像更大。
兰亭舟看着落了一叶的秋叶,淡淡地想,不知旦州府的静水深流之下,藏着什么怪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