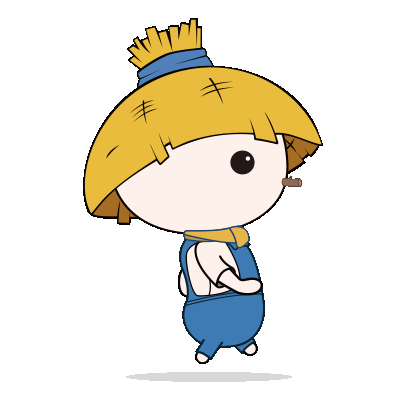我将黄茹芸的话转述给黄芙茵听时,她哭得泣不成声。她不解黄茹芸为何能这般轻易地放弃生命,更不解幼时那么要好的两人,怎么会成了现在这种结局。
但世上有很多事情都无法得出答案。
我只拍了拍她的肩以示安慰,告诉她,要带着黄茹芸的份儿一起活下去。
这个总是温柔笑着的少女擦干了眼泪,坚定地点下了头,眼里是前所未有的坚定。
或许经过这件事情,她也在不知不觉中成长了。
宰相十分守信誉,答应给紫刹果便给紫刹果,答应放我们出去,便干脆地叫人带我们进了密道,除去蒙在眼上的黑布,一切利落至极。
黄芙茵说这条密道是当年他们祖先为了避难而挖的,九曲八弯如迷宫一般,没有人带路根本出不去。她父皇当年待在这里一年多,得知有离开的地道后都不曾打听清楚就冒失地进去,可派人去查的时候,并未发现他的尸体。
她说她从未见过他,这辈子除去黄茹芸若还有遗憾的事情,便是没有见过生父的模样。
其实她比我还幸运些,我连生母都不曾见过,只是我生性冷淡,根本不甚在意。
他们虽然给了我们生命,但生活总是要靠自己活下去。
解开黑布看到外面的天空时,我竟傻傻愣了好一会儿,或许是错觉,我竟觉得陆地上的太阳比崖下要明亮许多,刺得我不住眯着眼,却仍舍不得移开视线。
周卿言向人打听了我们现在身在何处,当初落崖时我们在西南方向,如今却是在偏僻的北方,雇了马车南上,最快也只能在七天内到京城。
今日是十二月二十三日,离除夕夜只有七天。
接下来的日子可以说都是在马车上度过的,越临近京城,我与周卿言的谈话就越少,他似乎心事重重,我则是提不起劲,恨不得一日都不说一句话最好,直到第六日我们在靠近京城的一个小镇里吃饭,隔壁两人的谈话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隔壁桌一名书生模样的男子说:“你们听说没,傅将军的女儿找回来了?”
“傅将军的女儿?”同桌的男子狐疑地接口,“不是十五年前失踪了吗?”
“正是,可前几天刚认回来了。”书生大冬天还拿着一把扇子,好不做作地摇了几下,“听说将军夫人都哭得晕过去了。”
同桌男子仍保留态度:“这,该不会又是有人假意冒充吧?这几年上门认亲的人这么多,不都是贪图傅将军的身份!”
“哪能是冒充的,身上有信物呢!绝对错不了。”书生信誓旦旦,似乎就是当事人一般,“傅将军为国为民,在战场上威风凛凛,朝堂上也是功勋累累,最遗憾的不外乎一对子女之事,儿子八岁被杀,女儿八个月大失踪,实在是可惜。”
“唉,将军的儿子若是没有遭遇意外,说不定也会像他那样厉害。”同桌男子喝了口酒,又说,“那如今找回了女儿,将军和夫人肯定喜出望外了?”
“当然。”书生笑着点头,“将军摆了七天的流水席宴请京城内的人,无论你是达官贵人还是只是路边摆摊的,都可以去吃个痛快。”
“好大的手笔!”同桌男子赞道,“就是不知菜肴如何。”
书生咂了咂嘴:“那菜啊,真是美味可口,叫人恨不得将盘子都吞下去。”
同桌男子狐疑地看向他:“你这话是……”
“嘿嘿。”书生不好意思地笑了两声,“不瞒你说,那日我正路过将军府前,见那么热闹,就凑上去看了个究竟。”
同桌男子无可奈何地一笑:“我说你怎么这么清楚。”
“顺道,顺道而已。”书生摇头晃脑,“对了,你知道我在将军府看到谁了吗?”
同桌男子一脸郁结:“你说得轻松,七天的流水席,我怎么能猜到?”
书生露齿一笑:“近日刚被皇上封侯的那位。”
同桌男子思前忖后:“难道是五王爷家的三公子,最近刚被封为靖阳侯的那位?”
“正是。”书生神采飞扬地说,“靖阳侯相貌堂堂年轻有为,只站在那里就像从画里走出来一般,更不提他爹还是五王爷,以后定是朝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。”
“你去将军府难道只为了看靖阳侯?”同桌男子毫不留情地吐槽。
“此言差矣。”书生摇了摇手指,“我虽未听人说哪个是傅小姐,但见靖阳侯身边有一名貌美少女,看着也就十六岁的模样,与他有说有笑,一副熟稔的样子,再加上之前听人说见过他俩一起出行,便猜想那人就是傅小姐。”
同桌男子讶异:“靖阳侯与傅小姐?”
“正是。”
“可我听说李明堂的五小姐爱慕靖阳侯啊?”
书生立刻否认:“哪能啊,明明是靖阳侯与丞相都爱慕李小姐!”
我被口里的茶水呛了一下,抬眼看向一脸淡定的周卿言,他竟然也有爱慕的女子?他却一脸事不关己,仿佛他们嘴里谈论的根本不是他的事情。
同桌男子有些发怒:“不是你说靖阳侯与傅小姐一起出行的吗?怎么现在又成了他爱慕李家五小姐了?”
“京城里的王公贵族,哪能没点风流韵事!”书生摆摆手,“李家小姐虽然没了靖阳侯这个追求者,不还有李丞相吗?他可一点都不比靖阳侯差,论本事的话可能比靖阳侯还要厉害。”
同桌男子闻言点头:“嗯,就是名声不大好,说是长相似男似女,而且喜欢包养男童。”
一个不小心,刚吞下的米饭就呛得我直岔气,不住咳嗽了起来。对面“似男似女、爱包养男童”的周卿言正泰然自若地用着米饭,丝毫不被这些评价影响。见我咳嗽只稍稍抬眼,一副瞧不起我的神情。
我只好咽下惊诧,继续用餐。
隔壁桌两人还在交谈。
书生皱眉:“是啊,可虽然如此还是极得皇上看重。”
“皇上岁数与丞相相当,估计是这个原因。”
“有道理。”
随后他们便扯了其他的事情闲聊,不再围绕“王公贵族”的风流韵事。我也乐得安生用饭,不需要竖起耳朵听这些八卦。
上了马车后,周卿言闭目小憩,不知过了多久突然问我:“你可知靖阳侯是谁?”
我虽不明白他为何如此问我,但还是认真回答:“不就是同你一起爱慕李家五小姐的那名青年才俊吗?”
他微微睁眼,黑眸带着笑意:“莫不是你吃味了?”
我笑了笑:“吃味两个字怎么写?”
他眉目如画,神情有些不是滋味:“总有你吃味的那天,虽然……”下面的话却是没再说了。
我讶异他也有言语不利落的一天,却没有继续追问:“明日就到京城了,你有何感想?”
他轻轻叹了口气:“还真有些舍不得在林中的日子。”说罢看了我一眼,其中意思不言而喻。
我自然知他是说当时我与他单独相处:“叫马车掉头去崖边,我送你下去就是了,不用谢。”
他笑了笑,说:“回府后我可能要忙上一段时间。”
“嗯。”身为一国之相,离开半年还没有忙的事情,那未免太过惊人。
“你在府里,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玉珑。”
“嗯。”
“有想做的事情,也可以叫玉珑陪你。”
“嗯。”
“若想我了就夜里来找我。”
“……”
第二日傍晚,马车终于赶到了丞相府门口。来时虽隔着帘子也能听到大街上欢闹鼓舞,一派欢乐气氛,丞相府前却冷冷清清,不仅门上没有贴上倒“福”,连红灯笼都不曾挂上,若不是门口守着四名家丁,我都要以为这是处无人之宅。
我走上前,对其中一人说:“这位大哥,请问玉珑姑娘可在?”
家丁精神萎靡,闻言有气无力地说:“找玉珑姑娘?报上名来。”
“你就说沈花开找她。”
“大过年的还找上门,别是穷亲戚吧。”家丁咕哝了几声,慢吞吞地往里走,“等会儿啊,我去叫一声。”
大约过了半刻钟,便见玉珑急匆匆地跑来,身后跟着一名俊俏少年以及许久未见的马力。
“花开!”她见到我时失声大叫,脸上满是不可思议,“竟然真的是你!”
我好整以暇地笑笑:“玉珑,金陵一别已有月足,你可还好?”
她早已冲了上来,上上下下摸着我的脸:“好,好,你还是热的,你是热的。”
我哭笑不得:“我自然是热的。”莫非以为我是鬼魂不成?
“没事就好。”她红了眼眶,忍着眼泪说,“我还以为你已经……”
“沈姑娘,”相比起玉珑,马力就要沉稳许多,只是那双眼里又何尝没有期盼,“既然你还活着,那主子呢?”
我稍稍安抚了玉珑,对他说:“他没事。”
马力眼中浮现狂喜,看了眼身后的马车:“莫非……”
我点头,笑说:“他在马车里。”
玉珑更凶地哭了起来:“花、花开,你没在开我们玩笑吧?”
“自然没有。”我回头叫了一声,“周卿言,出来吧。”
里面的人缓缓掀起车帘,优雅从容地下了马车,笑说:“好久不见。”
马力神情一动,立刻就想冲上前去,站在他身边的少年却蛮横地撞开了他,欢喜地冲到了周卿言的怀里,大声喊道:“哥哥!你回来了!”
周卿言任少年抱住自己,脸上竟露出了从未见过的宠溺表情:“子逸。”
“哥哥,我就知道你不会死!”名叫子逸的少年更加紧地抱住他,喜极而泣,“你说过今年会陪我一起过年!”
周卿言笑笑,说:“我这不回来了吗?”
马力此时也已上前,平日里总是沉稳的脸庞掩不住欣喜:“主子。”
周卿言会意颔首:“我回来了。”
玉珑拉着我上前,又哭又笑地说:“原先还想着今晚团圆饭别吃算了,若不是李管家坚持,主子回来怕是连顿好吃的也没有。”
说着一名年约四十面容慈祥的男子上前,恭敬地低头,说:“主子。”
周卿言的眼神温和,浅笑说:“管家,这半年里辛苦你了。”
“哪里的话。”管家眼中也隐约泛着泪光,笑说,“主子回来就好。”
“好了。”周卿言拍拍怀中少年的背,示意他松开,“我们进去吧。”
少年这才松手,却还是紧紧跟在他身侧:“是,哥哥。”
回头时才发现门口已经挤满了人,仔细数数应不下于六十人,他们个个神情激动,异口同声地喊道:“主子,您回来了!”
我不禁看了他一眼,却见他也正看着我,视线对上后翩然一笑,挥手对众人说:“散了吧。”
“是,主子!”
我与玉珑进去时,敏感地察觉到有一道带着敌意的视线看着我,不怎么费劲就找到了那道视线的主人——竟是那叫作子逸的少年。
他年约十二岁,皮肤白净、相貌俊秀,身形和阿诺差不多高,一边跟在周卿言的身边,一边用不怎么友善的目光打量着我。
我心里微微讶异,不知何时惹到了这少年,玉珑却挡住了他的视线,轻声说:“不要介意。”
我自然不会跟个如阿诺一般年纪大的少年见识。
进屋之后周卿言被众人环绕簇拥,可还是吩咐玉珑说:“你带花开去沁竹院,安置好后再来膳厅用膳。”
其他人听得这话分明一愣,玉珑却极快地反应过来,笑逐颜开地说:“遵命,主子。”
玉珑领着我往沁竹院走,一路上不停地问着我与周卿言离开金陵后发生了什么,我简单向她描述了崖下期间发生的事情,她啧啧称奇,说我与周卿言命不该绝,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
我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:“方才那少年莫非是周卿言的弟弟?”周卿言与杨呈壁聊天时曾说过自己有个十一岁的弟弟,不过因为洪灾被水冲走了,鉴于他经常编故事的前提,后面半句可以忽略不计。
玉珑摇头:“子逸少爷并不是主子的亲弟弟。”
“哦?”我惊讶地挑眉,如果不是他的弟弟,他又怎么会露出那么宠溺的表情?
玉珑停在一所屋子前,打开门点起蜡烛:“子逸少爷虽不是公子的亲生弟弟,但公子待他比亲生的还好。”
我不禁打了个哆嗦,难道客栈里那两人说的……是真的?
“瞧你这表情,该不是想歪了吧?”玉珑没好气地看着我,“子逸少爷是主子救下来的,跟主子姓周,到现在也有三年了,这几年里他们与亲生兄弟无两样,并不是外人说的那种肮脏关系。”
我笑了下:“连我想什么都知道,玉珑越来越厉害了。”
她哭笑不得地说:“你一副主子不是好人的表情,我猜不到就有鬼了。”
她叫了几个丫鬟来,吩咐她们打扫房间以及替我准备洗浴衣物,等等,接着与我一起坐下,皱眉说:“子逸少爷脾气不大好,你以后能躲就躲着点。”
我点头:“好。”那子逸少爷一脸目中无人的样子,恐怕只有在周卿言面前不敢放肆。
“还有,”玉珑捂嘴偷笑了下,“我虽不知道你与主子间发生了什么,但是这座园子,本身是要给丞相夫人住的。”
我的下巴差点没掉下来:“什么?”
玉珑笑眯眯地说:“这园子就在主子园子的隔壁,是给主子未来夫人住的地方。”
难怪那些人听到周卿言安排我住在这里时都愣住:“我与他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,不过是主仆而已。”
她却不甚在意:“我只听主子的话,主子说什么便是什么。”
我……也罢。“我能换个地方住吗?普通的园子,和其他人住在一起也无妨。”
“不能。”玉珑想也不想便拒绝说,“主子叫我带你来这里,你就得住这里,不然主子会怪罪于我。”
她都这样说了我只好应下:“好。”转眼又想到一件事,“路遥有消息吗?”
玉珑眼神暗了暗:“不曾有路遥的消息。”
说话间丫鬟已将洗浴的所有东西都备好,玉珑说:“需要我派人帮你洗浴吗?”
“不用。”
“那我在这里等你,等你好了之后一起去膳厅。”
“好。”
奔波了这么久后终于能安心地洗一个澡,实在是难得的享受。如今我不用陪周卿言去算计人,身上也不再有折磨人的剧毒,一切似乎都豁然开朗。
想着想着,我竟然在浴盆中睡了过去,直到玉珑在外喊我时才倏然转醒,从已经冷掉的水中起身,换好衣物后走了出去。
等将所有的事情弄妥,已是一个时辰之后。
玉珑带着我去膳厅,到时周卿言与周子逸已经就座,李管家与马力站在一旁,另有四名长相清秀的丫鬟候在边上。
周卿言还未开口,便听周子逸冷哼一声,说:“叫所有人等一个,好大的面子。”
他这话自然针对我。
我没有还嘴,毕竟是我不对在先,走到周卿言身前淡淡地说:“抱歉,方才耽搁了点时辰。”
周卿言没有责怪周子逸也没有给我脸色,笑说:“来了就好,开始上菜吧。”
周子逸狠狠瞪了我一眼,稚嫩的脸庞满是敌意。
周卿言说:“都坐下吧。”
李管家与马力、玉珑没有推辞,极度自然地坐下,我见状走到玉珑外侧,正欲坐下时却听周卿言说:“慢着。”
周子逸脸上一喜,连忙附和说:“你什么身份,这儿哪里有你的位子?”
我愣了愣,随即起身往后面站,既然如此,待会儿等他们吃完再去用饭好了。
周卿言用眼尾瞥了他一眼,接着看向我,俊脸竟有些生气:“沈花开。”
不过是刚回府而已,要不要这么大的脾气?
“在。”
他长眸微闪,说:“你过来。”
我依言走了过去,不卑不亢地看着他。
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,眼中闪过一丝无奈:“坐下。”
啊?
“我叫你坐下。”他伸手拉住我的手腕,微微施力往他身侧的位子带下,“坐这儿。”
周子逸瞪大眼睛,随即不依不饶地说:“哥哥,她怎么可以坐在你……”
“子逸,”周卿言语气有些冷,面上却还是带笑,“吃饭。”
周子逸委屈地闭嘴,眼里却更为愤怒。
我实在是头疼,不过一顿饭而已,为何吃得这么不省心?
幸好接下来他没有再闹,一顿饭总算吃得安安稳稳。
散席之前,周卿言叫住了玉珑:“往后你就去花开房里。”
玉珑眨了眨眼,了然地说:“是,主子。”
我刚好些的头却又疼了起来,叫玉珑先走,我与周卿言再说几句话。
我揉了揉眉间:“你这是什么意思?”
他神色自若,反问:“什么什么意思?”
“周卿言,你明知道我说什么。”
他眯了眯眼,缓缓地说:“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说话。”
“好。”我说,“主子,不用派人服侍我,我不过一个护卫而已。住的地方也不用单独给个园子,与其他人一起住就好了。”
他悠然自得地笑了一声:“你是不是忘了那日我对你说的话?”
我脑中立刻跳到那日他狂怒时的画面,沉默了会儿,说:“记得。”
“记得就好。”他走到我面前微微俯身,脸庞离我极近,“那日我说的话你可以不当真,我却不能,我不逼你做任何事,但你也不能阻止我要做的事。”
说罢不再看我一眼,离开了膳厅,只剩我傻傻站在里头,心底滋味百千。
他这番话……何尝没有道理?
我既想不出反驳他的话,只好暂时妥协,在沁竹院住了下来。玉珑与我早就相识,相处起来自然没有难度,只是回到丞相府后我似乎不再是周卿言的护卫,不仅不用一天到晚守着他,还可以到处玩耍,身份与从前大不相同。我想与周卿言交流此事,玉珑却说他最近忙得天昏地暗,连吃饭都顾不上。她这般说,我自然不好去打扰他,只能盼着他有空时来找我。
一晃已是两个月余。
两个月里我一如在山上时每日的行程:早起练功打坐,吃早饭,在山上园子里逛逛走走,吃中饭,练功,刻木雕,用晚饭,练功,陪淘淘、小白玩耍,洗浴,睡觉。
这样的日子在玉珑看来无聊至极,我却早已习惯并乐在其中。
今日我吃过中饭在院子里打坐,却难得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
“土包子,这么大个园子住着肯定特别开心吧。”周子逸一进院就嘲讽地开了口,幼稚的脸上带着完全不相符的成熟。
我只淡淡看了他一眼,便合眼静心打坐,不打算搭理他。
他十分不满意我的态度,挑衅地说:“怎么,不回嘴?是被我说中了吗,土包子?”
我呼吸匀称,完全不受他影响。
他语气开始有点烦躁:“臭女人,再不吭声小心我揍你。”
我能感觉到体内的余毒已清,功夫也几乎全部恢复。
“你给我说话!”他气急败坏,伸手向我甩来,只是我闭着眼都能抓住他的手,随即不轻不重地扔开,睁眼淡淡地说:“有什么事?”
他满脸恼怒,恶狠狠地说:“你这个贱人,给我哥哥下了什么巫术,竟然叫他对你如此关照?”
这人说话实在称不上好听。
他见我不说话,更是暴怒:“我叫你说话!”
“你要找的是你口里的‘贱人’,我不姓贱,也不叫人。”
“你!”他没料到我会反击,当下甩了下袖子,“好个伶牙俐齿!我倒要看看你今后还嚣不嚣张得起来!”说罢阴险一笑,哪里是一个才十二岁的少年。
他离开后不多时,我也出了院子,难得想去京城街上走走,谁知半路上见他正用各种恶毒的字眼骂着一名少年。那少年背对着我看不清容颜,但单薄的身子微微发抖,不知是在忍耐还是哭泣。
周子逸越骂越凶,到最后竟伸手给了那少年一巴掌,少年歪过身子,看到侧过的半边脸叫我心头猛然一震。
阿诺!
我看到被打的少年竟是阿诺时当下呼吸一屏,大步迈着便朝他们走去,那边情况却有反转,阿诺嘴里骂了几声,站起身反手还了周子逸一巴掌,直打得他往后退了几步。
周子逸没料到他会还手,一双眼睛瞪得如铜铃般大小:“你这个杂种竟然敢打本少爷!”说罢恶狠狠地眯眼,抬脚就踹向阿诺,“今日我就叫你死在这里!”
“慢着!”我及时赶到,一把搂着阿诺走远几步,皱眉冷冷地说,“周子逸,住手。”
他见我与阿诺这么不避嫌,当下鄙夷地说:“贱女人,你还真是……”
“花开!”怀里的阿诺却大声叫了起来,满脸不可思议,“花开,你竟然在这里!”
我拍拍他的脸:“嗯,我在这里。”又看向周子逸,“他哪里惹到你了你要打他?”
周子逸的视线在我与阿诺之间来回打量,嗤笑了一声,说:“我打自己的小厮也要你来管?狗是我的,你管不着!”
我心中冷笑了一声,原以为以前的周卿言已经够让我动怒,哪知他这弟弟却更叫我怒火中烧:“那就不怪刚才阿诺给你那巴掌。”连最起码对人的尊重都没有的人,根本听不懂所谓的道理。
他一手抚上脸,阴恻恻地笑了起来:“你的意思是不会将他给我了?”
我任由阿诺害怕地搂住我的腰,说:“自然。”
“好。”他不仅没有发怒,反倒眉开眼笑起来,“这可是你说的。”说罢意味深长地一笑,便扔下我与阿诺走掉。
周子逸走后,我将阿诺从怀里拉出,一手抚上他被打肿的半边脸,轻轻地问:“疼吗?”
他明明眼眶含泪,却灿烂地笑说:“不疼!”
怎能叫我不心疼?
我牵着他往沁竹院走,问:“你怎么会在这里?”他不是该在山上的吗?
阿诺甩甩我们牵着的双手,扁扁嘴说:“你是坏人,不跟我们说一声就离开,也不告诉我们去了哪里。”
我微微叹气,其中的事情他又怎么能理解:“我有点事情,所以匆忙下了山。”
他委屈地说:“你下了山之后好歹锦瑟留在山上,可不出几天,锦瑟就跟着三师兄一起下了山,我原以为他们去一两个月就会回来,师母却说锦瑟这次可能要很久很久才回来,因为、因为,”他站定,眉毛愤怒地竖起,“锦瑟要和池郁去定亲!”
我不禁失笑,原来阿诺还惦记着锦瑟:“所以你就背着爹和娘偷偷下山?”
“嗯!”他苦下脸,悲情地说,“我听师母无意中说过他们来了京城,所以跟着顺路的人一起来到这里,谁知刚到不久就被偷了钱袋。在这里不认识人又没了钱袋,每天都挨饿受冻,幸亏丞相府的管家救了我,安排我进府里做事,然后,然后就成了周子逸的小厮。”
他拉上袖子露出了手臂上一块块的瘀青:“你瞧,这些都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掐的。”
我看得触目惊心,周子逸的脾气到底多坏,能将同龄少年的胳臂掐成这样?“方才呢,出了什么事?”
阿诺放下袖子:“方才我按管家的吩咐,正准备去外面买一些纸墨回来,半路上就碰到了他,我已经说明了是管家遣我去跑腿,他却一口咬定我偷懒出去玩,我解释了几声,他就给了我一巴掌。”
我听得直皱眉头,嘴里说:“吃了这些苦,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一个人乱跑!”
他搓了搓鼻子:“要不是为了找你们,我才不会下山。对了花开,你怎么会在这里?”
我简单地说了下:“我做了丞相的护卫,自然跟他回来了。”
“原来是这样,哈,我们俩真有缘。”他边走边拿脑袋蹭我的手臂,“花开,你见过未来的丞相夫人吗?我听别人说她住进沁竹院了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