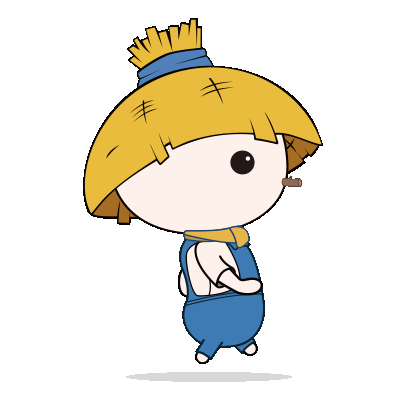“你要我?”我深深看了他一眼,“你到底要我做什么?”
他愣了下:“我要你……做什么?”他突然低声笑了起来,在安静的午夜大街上显得分外突兀,“我要你做什么吗?”
我没有被他的愉悦感染,面无表情地说:“要我做什么开口便是了,不用拐弯抹角。”
“你倒是利索得很。”他止住笑,饶有趣味地说,“要你做什么,我暂时还没想到。不过……你就不曾怀疑过我要你是因为对你有情?”
“情?”我怪异地看着他,“你对我用情?”
他点头:“正是。”
“什么情?”我冷静地问,“亲情,友情还是爱情?”
“自然是爱情。”他说得流畅至极,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。
我不打算遮掩自己的不以为然:“你不如跟我说牛正在我上空飞过,也好过这个笑话,冷得一无是处。”杨呈壁如此待他都能被他利用,卞紫苦苦追求于他也未得到他正眼瞧过,更重要的是,即使他利用了其他人,他也能毫无愧疚之心,视一切为理所当然。别说爱情,在他身上,我甚至怀疑是否有“情”这字的存在。
“花开,我就是喜欢你这副模样。”他低垂眼帘,眼神专注地盯着我,“小小年纪却没有世俗女子的自作多情,叫我好生佩服。”
不自作多情是因为我一直都知晓自己有几斤几两。
“我再问你一句,”他伸出手指,撩起我胸前一缕发丝把玩,“我这样对你和杨呈壁,你可恨我?”
我只想了一下,便诚实地摇头:“不恨。”
我厌恶他的手段,却不恨他这个人。
一面极度厌恶他利用别人,一面却克制不住地佩服他这种心态。着实天上地下,唯我独是。
世上能做到这样的人,恐怕也只有他周卿言一个。
他是强者,真真正正的强者。
我佩服强者。
“有你这句话便足够了。”他又低低地笑了起来,“沈花开,你可知道你有多么独一无二?”
“这世上无论谁都是独一无二的。”
“你和他们不一样。”他摇头,“我原以为你对事冷漠,却不料你重情重义,我原以为你经过昨日之事,说不上对我恨之入骨,但难免会带上私人情绪,没想到你竟能跳脱开来,冷静看待此事。你若身为男子,必有一番作为。”
能得到周卿言如此夸奖,实在是我的荣幸。只是……“我依旧讨厌你。”我眼都未眨,如是说道。
他不以为意,笑说:“讨厌我又如何?只要能为我所用便可。”
“我何时才能恢复自由之身?”
他想了下,没有给我确切的答案:“等到我愿意让你走的那天。”
我与他签了三年长约,如今又因杨呈壁的事情要我继续留在他身边,想来恐怕不下于五年。这样一来,我原先周游各地的打算……何日才能实现?
我躺在床上睁眼放空,前所未有地轻松。
一切似乎都已风平浪静。
杨呈壁不会再突如其来地找我,卞紫不会再向周卿言哭哭啼啼,周卿言也不用再费心设计与杨呈壁一次又一次相聚。
花开,以后再也不要轻易对人用情,尤其是周卿言身边的人,以防真有一日对他恨之入骨。
对人用情不好,对人恨之入骨更不好,对周卿言这种人恨之入骨则是不值。
一个人独善其身,何其自在!
玉珑在门外敲门:“花开,在吗?”
我起身:“进来。”
玉珑推门进来,表情有些忐忑:“花开……”
我走到桌边坐下:“坐吧。”
她在我身边坐下,一时间也不知要说什么。我替她倒了杯茶,主动开了口:“是为了周卿言的事情吗?”
“花开,我没有骗你,我真不知道主子要做的竟然是这样的事情。”她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,“当初主子回来只说皇上给了他半年的时间休息,接着便带我们来到金陵游玩,谁知他暗地里还是在查案。”
我耸肩:“我相信你。”周卿言要做的事情自然不会一一禀告他们。
“真的吗?”她松了口气,继续说,“其实主子并不是个坏人。”
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后再说这句话,可信度实在太低。
“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,但我还是要说。”玉珑低眉,似是陷入了回忆之中,“当年杨呈壁放我走后,我因为怕被追捕,所以扮成了疯疯癫癫的乞丐以求保命。从金陵到京城,一路上对人行乞,有和颜悦色之人,也有朝我吐口水骂我的人,那几个月里,我当真见过了世间百态。我原以为最糟糕的不过如此,却不料在京城遇上了一帮乞丐,见我是个疯婆子竟然想……”她顿了顿,厌恶地说,“即使我丑陋不堪肮脏不已,那帮畜生也想占我便宜。他们拖我入了巷子,不管我如何挣扎都不肯放我走,我大声呼救,也有人好奇地走到巷子看个究竟,却没有一个人上前相救,都只当看戏一般看了一眼就走。”
她脸上浮现一种悲凉:“你可知那时的我有多么绝望?”
我能想象到那种情况下她的心情,大仇未报,清白也将不保……身为女子,天生的弱处实在太多。
“我甚至已经准备好咬舌自尽。”她苦笑,“然后便见那些乞丐一个个地被人踢开,像破娃娃般躺在地上不能动弹。那人将身上的披风解下来丢在了我身上,对我说:‘如果没死,就将披风盖好。’”她想到这里笑出了声,“是不是听着十分无情?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,实在是天籁之音。”
“我抬头时才看清他是什么模样,说实话,看着的确不像好人。”她喝了口茶水,“他见我还有意识,笑了笑又说:‘愿意跟我走吗?’我明明觉得他很危险,却不自主地点下了头,似乎看到了他的笑便无法再拒绝什么。”
“我选择了跟他走,成为现在的玉珑,代价则是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,都不要再去执着。”玉珑眨了眨眼,泪光隐隐浮现,“我舍弃了为爹和娘报仇,换来了现在的安稳生活。如今主子抓了杨德志,虽然不是为我,却也让我了结一桩心事。”
她垂眸,泪珠沿着脸颊滚落:“主子是我一辈子的恩人。”
依玉珑的话来说,周卿言确实做过好事,但这是在玉珑不计较他所得的情况下而言。对周卿言来说,只是随手救个人便有了个美貌贴心的丫鬟,并且忠心耿耿,何乐而不为?不过对于玉珑来说,也的确不用去计较周卿言的目的,只要结果好便是好。
“我知道主子很看重你,所以不希望这件事让你对他产生偏见。”
何来偏见之说?我对他的不喜从来都是正面得出。
“我也明白这点事情不足以让你对他改观,但只要你和主子慢慢相处,定能发现他好的地方。”
他好又与我何干?我和他不过是主子与护卫,保持这层关系便是最好。
“明日我们便要准备回京了,不过主子和你还有路遥会另外离开,希望你能好好替我照顾主子。”
照顾这事情我干不来,我所能做的只是保护他不挂掉而已。
“我得回去了。”玉珑擦了擦眼泪,“主子今日出门救了个姑娘回来,我得回去照顾她。”
我点头:“好的。”
玉珑起身往外走,嘴里还说着:“说来也巧,主子半年前在临安救过她一次,如今在金陵又救她一次,看来和主子缘分不浅。”
我闻言霎时间愣住。
玉珑说的这人难道是……
“这姑娘是不是你前几日在布店遇上那男子的师妹?”我抓住她的手腕,脱口而出。
玉珑惊讶地看着我:“你怎么会知道?况且,你那日不是没有看到池公子吗?”
我哪里还有时间跟她解释这些:“那位姑娘现在在哪里?”
她见我反常,也不再多问:“我正好要去那里,你跟我一起去吧。”
我与玉珑到那里时,还未进门便听到有女子娇声在说:“我师兄在忙,所以才一个人偷溜出去玩,谁知道又会遇到危险。”
这声音如此熟悉,我又怎么可能听不出来是谁?
我未打招呼便推开了门,眼神定定地落在说话那人身上。那人见到我也是一愣,随即欢喜地叫道:“花开!”
周卿言习惯性地眯眼,视线在我和锦瑟间来来回回:“你们两个认识?”
我还未开口,锦瑟便抢着说:“何止认识,对吧花开!”
周卿言似笑非笑地睨着我:“哦?”
我恭敬地低头:“多谢主子救了舍妹。”
“妹妹?”玉珑惊讶不已:“这位姑娘是花开的妹妹?”
“正是,而且是亲妹妹。”锦瑟笑眯眯地走到我身边,挽着我的手欣喜地说,“没想到你竟然在这里!”
我对周卿言说:“主子,能否让我和舍妹单独待一会儿?”
周卿言看我的眼神意味深长,却没有多问,只颔首说:“那我们就出去了。”
他带着玉珑离开了房间,屋内只剩下我和锦瑟。
锦瑟虽然欢喜,却仍有些不悦地说:“花开,你实在太不够意思了,刚过完十六岁生日就抛下我们所有人下了山,半年里毫无音信,若不是我今日被周公子所救,恐怕也不知道你竟然在周公子身边。”
锦瑟这番话,说得似乎待在周卿言身边是件极为幸福的事情一般。她自然不知他的脾气有多么阴晴难辨,也不知我在他身边被利用了多少回,更不知下山那事并不是我所愿,而是娘开口叫我离开他们。她似乎也忘了我生日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,导致了什么事情。
也罢,记性不好的人,知道越少的人,总是活得更为开心。
我没有回答她的话,问:“你怎么会在这里?”
她松开手,站在原地转了一圈:“你看这身衣服好看不?”
“嗯。”她今日穿了一身桃色棉裙,领口一层白色绒毛,映得她姣好的容颜更为活泼可爱。只是这与她在金陵有何关系?
“我听人说金陵出产的布是全国最好最漂亮的,于是让师兄带我来这里做几身衣裳,谁知道一来这里就生了病,久久都不见好,这身布还是师兄替我去挑的呢。”她得意地再转了个圈,“你说师兄挑得怎么样?”
“极好。”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玉珑会在布店遇到池郁,但锦瑟又不在身旁了。原来他们俩是一起来的金陵。
她不知想到了什么,突然安静了下来:“花开,那个……”
“怎么?”
“师兄这次带我下山,是为了带我去京城见他爹娘。”
我心里一震,面上却努力扯出笑容:“这样吗?不错。”池郁终于要带她去见爹娘了吗?估计很快就要定亲了吧。
她脸上却有着苦恼:“可是,可是……”
我见她这副神情,心里隐隐有些怀疑:“可是什么?”
“花开,我记得你在山上时对我说的那番话。”她幽幽叹了口气,好不为难,“你走后的半年里,我也很努力地去忘掉周公子,和师兄好好相处。今日之前,我真以为我已经忘了他。”
锦瑟说这番话的意思是……“锦瑟,你今日根本没有昏迷,是故意昏倒的?”
她诧异了下,很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:“花开,果然还是你了解我。”她不知所措地绕着手指,“我只是想和他多相处一会儿,多了解他一点而已。”
我简直不知该如何说她:“你当真记得我那日说的话?那你可记得我曾提醒过你,你身边还有个师兄?”
锦瑟有点被我吓到:“花开,你干吗这么凶?我只是说笑而已,我当然记得我有师兄。”
说笑?“如果是说笑最好。”我冷淡地说,“锦瑟,别做出糊里糊涂的事情。”在池郁要带她回去见爹娘的当下,她竟然还对周卿言念念不忘,如果是真的,该是多么糊涂的一件事。
她吐了吐舌头,撒娇地说:“好啦,我不跟你开玩笑了,我也不在这里待了,师兄还在客栈里等我呢,再不回去他该着急了。”
她抱了我一下,又如蝴蝶般轻易地跑到门口,似是玩笑地说:“如果是师兄不要我了,我是不是就能堂堂正正地喜欢他了呢?”
她说完便急匆匆地跑了出去,根本不打算听我的回答。我只能原地叹了口气,暗暗想着明日我们离开金陵后,事情会有一些转机。
我没想到半夜里有人敲开了我的门,而那人竟然是……池郁。
深更半夜里,他就那样悠然自得地站在门口,温柔浅笑地看着我说:“花开,总算找到你了。”
我此时的心情实在是难以言喻。
我喜欢池郁毋庸置疑,迷恋他曾带给我的温暖,却也怨过他利用我来刺激锦瑟,只是半年前的难过到此刻竟然淡了许多,平日里的想念到真正见了面时,也只化成一句淡淡的“师兄”。
他似乎已经习惯我的冷淡,低低叹了一声,说:“半年不见,还是这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。”
我仰脸看他,他也与半年前毫无变化,仍是那般温文儒雅,清俊得让人不自觉地想亲近他。
他伸出食指轻轻触碰我的脸颊:“怎么,不认识我了吗?”
我木然地摇头,突然想起那日离开时在他门前放下的木雕,不知他是否察觉了……这般想着,却又立刻否决。知道了又如何?那日我对他的喜欢便已经埋了起来,一心祝福他和锦瑟能百年好合。
只是说到锦瑟……
我眼神微冷,问:“师兄,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?”
“随便找个人问下不就知道了?”
我皱眉:“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。”
他愣了下,莞尔笑说:“花开,你竟然变了。”
我低头看了下自己:“哪里?”
“下山不过半年,气势竟然凌厉了起来。”他仍在笑,眸色却渐渐变深,“是由于跟在他身边的缘故吗?”
“师兄看错了吧,我还是和从前一样。”
“兴许。”他看了眼屋里,缓缓地说,“花开不请我进去坐坐吗?”
我这才意识到竟然让他一直站在门口说话,连忙请他进屋:“师兄请坐。”
池郁在桌边坐下,细细打量了屋里一番:“今日锦瑟回到客栈便有些心神不定,我料想她肯定遇上了什么事,一问才知道她竟然在这里碰到了你。”
因为碰到了我,所以才心神不定吗?恐怕我只是附带,真正叫她心神不定的另有他人。
我又想到她离去前说的那句话,什么叫作“如果是师兄不要我了,我是不是就能堂堂正正地喜欢他了呢”?
我怔怔地看着池郁,难道锦瑟心里想的是……
“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?”池郁有些莫名,打趣说,“难不成是想我了?”
我却没有和他玩笑的意思,如果锦瑟当真那样想,池郁可就悲惨至极了。都已经到了要带她回去见爹娘的当下,她竟然还做这样的事情,实在是叫人……叫人无法接受。
我还记得那日她在月光下抱着池郁,信誓旦旦地说从今往后只喜欢他一人。可再见周卿言一面,她却将这些都抛在了脑后,心里想的念的又是另一人。
我不信聪明如池郁会没发现她的改变。
罢了,发现了又与我何干?他们的事情,我还是不要掺和的好。
“从方才起就一句话不说,在想什么呢?”池郁拍了拍身边凳子,示意我坐下,“小白和淘淘呢?”
我从床底将笼子拿了出来,笼内小白和淘淘相互依偎睡得正熟,自然不知道久违的池郁正看着它们。
“好些日子不见,这两个小家伙也长大了些。”池郁打开笼子摸了摸它们,见它们没反应又将门关上,放到了桌旁。
“嗯,确实长大了些。”我虽然当了护卫,但给它们吃的丝毫不差,加上清然喜欢逗弄喂食它们,这半年里它们可是幸福至极。
“你呢,花开?”他笑着,清俊的脸庞在烛火的映照下更为温暖,“这半年里过得怎么样?”
我看着他,一瞬间冲动地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,下山、钱被偷、来风月阁、跟随周卿言、认识杨呈壁……只是最终却只是短短的一句:“挺好的。”
他眼中闪过一丝失望,叹了口气说:“对我也还是这么言简意赅。”
我低着头,不住地拨弄着手指:“师兄呢,过得怎么样?”
“老样子。”他笑笑,墨黑的眸里似乎有些落寞,“除去身边没有花开,一切都是老样子。”
这句话说得实在容易让人误会,只是他的话,我已经不会再去当真。
“师兄认识周卿言吗?”我自然没忘记玉珑上次说的那些话,周卿言与池郁早已认识。但周卿言贵为丞相,自然不会与普通人结识,那么池郁又是谁?
“嗯。”他笑容淡了下来,“说到这个,你怎么会在他身边做事?”
我替他倒了杯茶:“机缘巧合。”我与周卿言间的事情,又岂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?
他沉默了一会儿:“花开,跟我们一起走吧。”
我愣住,呆呆地望着他,不知该做何反应。
他修长的手指掠过我胸前的发丝,最终还是空着收回手:“他太危险。”
他叫我离开周卿言,因为他过于危险。可他又怎么知道,对于我来说,他才是最危险的那个。
“你现在不用回答我,”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,试图消除我的焦虑感,“今天我先回去,明日同一时间我会再来,到时候告诉我你的答案。”
我起身跟在他身后:“师兄,慢走。”
他走到门口时停下,缓缓转身,眼中闪过一丝若有若无的无奈:“花开,待在我能看到你的地方,好吗?”
我在心底缓缓地摇了摇头。
我怎么可能待在能看到你的地方?如果可以,我甚至想这辈子都不再见到你。
我从不怕周卿言无情,我怕的是自己对你多情。
只要远离你,我就能慢慢忘掉自己对你的喜欢,一点一点,直到那些喜欢成为记忆中的美好片段。然后终有一天,我会遇上另一个人,或许不再有这样美好的爱恋,却愿意和那人共度一生。
我没有告诉池郁,第二日我便要跟着周卿言一起离开。他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应该明白,我的回答究竟是什么。
娘当时的做法没有错,我离开确实是最好的办法。三人的关系里,我的位置实在太过尴尬。
我走的时候,天空难得放晴了一回,阳光暖暖地洒在每个人身上,连带让心情也稍微好转了一些。
武夫人似乎早已料到我会离开,对此没有多大的情绪波动,只叫我出了事情尽管回来找她。清然则是哭哭啼啼,十分不舍我的离去,非让我保证以后每年都要回来看望她一次。
真是个长不大的姑娘。
不管如何,我今日就要离开这个待了半年的地方,以后的路是怎样,我心里也没有底。不过有一样可以保证,那就是跟着周卿言,生活绝对不会平淡无奇。
被刺杀被谋杀被暗杀什么的,应该不会少吧。
玉珑晚我们一日跟着马力还有大部队回京,这边只有我、周卿言以及路遥,三人去找程令的尸体。路遥充当马夫,我和周卿言则舒适地在马车内休息。
昨日之事,周卿言并没有多问。他似乎对一切事情都不关心,只关心程令的尸体在哪里。
这样对于我而言是极好的,不要再过问我的过去,只在乎我的当下与未来。
马车在路上走了一天,直到傍晚才在荒野林间停了下来,路遥开始生火做饭,动作娴熟利落,实在叫我有些吃惊。
“你这样看我干什么?”路遥不耐烦地瞪我一眼,“没见过男人做饭啊?”
我诚实地摇头,确实没见过,而且是这么大块头的男人做饭。
“没见过世面。”他啐了口唾液,恭敬地喊道,“主子,可以用饭了。”随即又递了碗给我,“还不给主子盛汤?”
我看眼那碗,绕过身去替自己盛满,他见状大怒:“嘿,你个臭丫头……”
“路遥。”周卿言出声,适时地阻止了他。
“主子你这样纵容她,她会越来越无法无天的!”路遥恶狠狠地说。
周卿言斜睨了我一眼:“用饭吧。”
路遥只好闭嘴,不一会儿后又开了口:“主子,这一路上似乎有些不对劲。”
“怎么?”
“白日里我们一共经过三个城镇,我仔细瞧过了,每个城镇里都有不少乞丐,而且都是年幼残疾的孩童。我怀疑有人专门在干什么勾当。”
周卿言慢条斯理地咽下口里的干粮:“你看真切了?”
“自然真切。”路遥严肃地说,“我跟着主子去过这么多地方,见过的乞丐没有几万也有几千,但数量如此多的残疾孩童,还是第一次见到。”
“那几个分别是什么城什么镇?”
“雒阳城、宜风城与大都镇。”
“今晚先找个地方休息,明日再回去看看。”周卿言喝了口汤,“我吃饱了。”
“哎主子,你才喝了半碗汤啊!”
“太难喝了。”
路遥受了打击,咕哝说:“荒郊野外的,主子就将就下呗。”他忽然又看向我,“喝什么喝,这么难喝你还喝!”
我嘴里的汤咽也不是吐也不是。
“算了,喝吧喝吧。”他豪迈地挥手,“好歹还有个欣赏我厨艺的人。”
我艰难地将汤咽下:“我也饱了。”
路遥在身后急切地嚷嚷:“我跟你说笑,你别介意啊,还有半锅汤,总不能让我一个人喝完吧!”
我管你呢!
晚饭后我们又开始赶路,原本以为这种荒郊野外不会有住宿的地方,却不料在打算放弃之时看到了一家客栈。路遥十分反对去住客栈,说“方圆百里不见人烟这里却开着一家客栈,绝对是黑店”,对此周卿言却不以为意,坚持“黑店也比露宿野外要好得多。”
既然主子都开口了,我们自然收拾东西便走了进去。
店里掌柜正在打着算盘,见到我们时眼中飞快地闪过一丝欣喜:“三位客官,是要住宿吗?”
路遥冷哼一声,拿出一锭银子扔在桌上:“不住宿难道来逗你玩儿不成?给我来两间最好的客房,然后准备些热水。”
掌柜见到银子眼睛倏然一亮,连忙将银子收了过去:“好好好,这就替你准备。”他对一旁刚醒过来的小二使了个眼色,“带客官们去天字一号房和二号房。”
小二打了个哈欠:“三位客官这边请。”
掌柜的虽然说是最好的客房,其实也就是一间还算干净的小房间,不过有床睡总比睡马车里要强。我洗漱好后和衣躺下,不多时便进入了梦乡。
半夜却被一阵笛声吵醒。
笛声悠扬绵长,似哀怨又带着控诉,似情缠却带着痛楚,让人的心绪不禁随着它的音调蜿蜒起伏,仿佛亲身体会了那一场爱恨情仇。
只是听着听着却觉得精神恍惚,开始我以为是自己又乏了,不一会儿却意识到有些不对劲,这笛声分明在蛊惑人心。我立刻坐起运功,直到笛声停住,这才觉得意识恢复了清醒。
我立刻赶往周卿言的房间,刚进门却看到周卿言对我比了个“噤声”的手势,接着指了指地上的路遥。
路遥半睁着眼,眸内一片呆滞,哪里还有平日里的凶狠和蛮横!
我皱眉,看向周卿言,在他脸上得到了同样的疑惑。
这种荒郊野岭的客栈里,竟然有人会迷魂之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