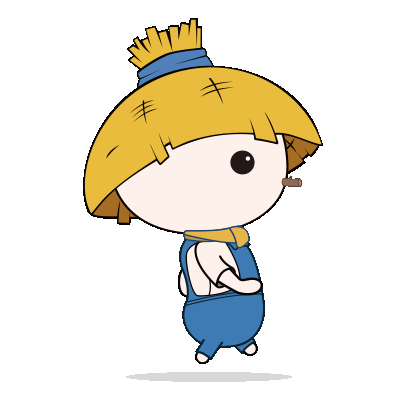刚从芝晴房间里出来,门外一直在看热闹的清然便扑了上来,一脸崇拜地盯着我,说:“花开!没想到你功夫那么好!”
我瞥了她一眼,自兀自地对杨总管说:“杨总管,没事的话我先回去了。”
杨总管说:“去吧,有事情再叫你。”
“总管,总管!”清然连忙举手,“我也要去休息会儿。”
杨总管瞪着她:“你个死丫头,一天到晚只知道乱跑,还休什么息!”
“我不管,都跑一天了,连口水都没喝上呢!”清然鼓着脸颊,嚷嚷着说,“我也要去休息,你待会儿有事情的话再找我呗。”
杨总管哭笑不得,故意骂了几句:“你个死丫头,待会儿要是找不到你就死定了!”
清然冲他做了个鬼脸,抱着我的胳膊便往前走:“走了走了,再不走就又有事情来了。”
我任由她拖着我往前走,等到了没人的地方才抽回了手:“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?”
清然的眼神有些闪烁,讨好地说:“那个,花开啊,你的武功很不错嘛,刚才几下就摆平了那个无赖。”
我双手抱在胸前:“别装了,你想干吗?”
“嘿嘿嘿,”她不好意思地干笑了几声,“这你都看出来了,花开你好聪明!”
我不理她的巴结:“别灌迷魂汤,你说还是不说?”
“说,我说。”她立刻来了精神,“我想让你陪我去看看那个周公子。”
我挑眉,周公子?“你看他做什么?”
清然笑得促狭:“我这不是好奇吗。”
我有些莫名:“有什么可好奇的,不就是普通的客人吗?”
“谁说他是普通的客人?”她神秘兮兮地趴到我耳边,“我听人说啊,这个周公子长得比卞紫还漂亮,而且身边带着一个不逊于卞紫的丫鬟和两个高得像熊一样的护卫,四个人站在一起,一看就不是什么普通人。”
我脑中立刻浮现那人的模样,结果竟发现他确实比卞紫更为貌美,可身为一个男子,样貌竟比女子还要美,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?
“而且啊,周公子出手可阔绰了。”她有些羡慕地说,“听说带他进楼的香婉拿了一两银子的赏钱呢!”
“一两银子?”我挑眉,随便给个赏钱都有一两白银?依我看那不是阔绰,是脑子被门给夹了。
“还有啊,这位公子是打算长住呢!夫人先把他安排在左边的厢房里,等后头的梨映院收拾好了再让他搬进去。”
听到这里我有些意外:“长住在这里?”外面是没有客栈不成!
“这个你就别管了,夫人也说了,这是个贵客,要好好招待。”清然对我挤眉弄眼,“最重要的是有银子收就好。”
说得也是,管他来这里是做什么的,有银子拿就是了。
“喂喂,你上哪儿去!”清然一把扯住我。
我打了个哈欠:“回屋睡觉。”
“别啊。”她撒娇地说,“陪我去看看那周公子到底长什么模样嘛。”
我凉凉地看她一眼,说:“不去。”
“去嘛去嘛。”
“不去。”
“花开,陪我去嘛,就看一眼,一眼就行。”
“清然,”我拨开她的手,郑重地说,“我已经看过他的长相了,所以,你自己去吧。”
我好不容易才打发掉了清然,回屋后将淘淘和小白从笼子换到了转轮里。许是关在笼子里久了,它们今天显得格外兴奋,短小的四肢奋力跑动,有种笨拙的可爱。
我趴在桌子上看着它们,等它们跑累了时便伸出食指摸摸它们,然后它们便会舒服地眯起豆粒大的黑眼睛,或用前爪挠挠脸,一脸惬意。再接着又忙不迭地开始奔跑,周而复始,乐此不疲。
我突然就有些感叹,淘淘和小白的生活一直都是这样,吃,喝,睡,跑,单调却舒逸,完全没有任何多余的烦恼。或许它们到现在都没发现,我已经带它们离开了山上,在山下开始了属于我和它们的新生活。
正感叹间,小白突然伸出舌头舔了舔我的指头,看我收回手后又回到了轮子上,肥肥的屁股对着我,一扭一动,好不可爱。
我失笑,无意间却看到手背上那条几乎快要消失的疤痕,心里顿时有种说不出的苦涩。
那年锦瑟缠着我带她去湖边玩耍,我只低头捉了条小鱼,抬头时却已经没了她的踪影,等我下水将她救上来时她的脸惨白吓人,完全没了平日里的淘气。我将锦瑟扛回去时娘吓得面色发青,她一眼都没看我,一把接过锦瑟后推开了我,急急忙忙地进了屋。
爹和师兄们赶到后什么都没说,只围在了锦瑟的床前,帮着娘忙前忙后。我也想帮忙,却不知能帮上什么,只能不停地捏着手心,沉默地站在门边。
不知过了多久,娘终于松了一口气,她摸了摸锦瑟昏迷中的脸,而后走到了我面前,并不恼怒,只淡淡地说:“花开,难道你不知道锦瑟不懂水性吗?”她说完便回到了锦瑟的床前,不再看我一眼。
我想说:娘,是锦瑟哭着闹着让我带她去的。
我想说:娘,我不是故意的。
我想说,娘,我也受伤了。
但我最终什么都没说,只是低头看着地面,许久,许久。
那晚有人敲响了我的门,让我惊讶的是,那人竟然是刚上山不久、和我没说过几句话的池郁。彼时他还是个清隽的少年,稍显青嫩的脸庞和笑容,温柔地对我说:“花开,把手伸出来。”
我伸出手,他却摇头,拉过我垂在身后的那只手。
“是救锦瑟时被镰草割伤了吧?”他垂眸,长睫在眼下形成一小片扇形的阴影,“很疼吗?”
我怔怔地看着他,过了一会儿才缓缓摇头。
他却笑了出来:“花开,你真傻。”他从袖子里拿了一管药膏出来,轻柔地替我擦上,“即使疼,也从来不说出口。”
我一句话都没说,任由他替我涂好药膏,然后无奈地摸了摸我的头,说:“以后疼的话可以告诉我。”
我将脸埋进手臂中。
你说疼的话可以告诉你,但这么多年来,我竟然已经忘了什么样的感觉才是疼。
这日早上我照旧早起,在林间练了约莫一个时辰的功,刚坐下调息便听到有人说:“姑娘似乎武功很好。”
我睁眼,面前是一名女子,样貌清丽脱俗,一袭淡藕色的长裙,衬得她有几分不食人间烟火。让我奇怪的是,我竟觉得她的声音有些熟悉,但我也未多想,问:“这位姑娘是迷路了吗?”
女子微微诧异: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
我说:“我看姑娘面生得很,似乎不是阁里的人,而且方才半个时辰里,姑娘已经路过这个林子三次了。”
女子掩唇一笑:“竟然都被你看到了,真是丢脸。我确实是这几日才住进来,对这地方不熟悉,一出门就忘了方向,到现在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。”
我说:“姑娘要去哪里?”
“梨映院。”
“你沿着左边的路一直走,等到一个十字路口后往左拐一直走,看到一座小桥时过桥,过桥后往右边走半刻钟便到了。”
她仔细地听着,笑说:“真是谢谢你了,不然我不知还要绕多少趟才能找到回去的路。”
我摇了摇头:“不碍事。”
女子走后没多久,清然便找了过来,只是这次不像往常那样兴冲冲,而是满脸急色。“花、花开。”她气喘吁吁,断断续续地说,“你、你、你赶紧去一趟梨映院。”
我挑眉,怎么又是梨映院?“怎么了?”
“打、打起来了!”她好不容易才挤出这几个字,“夫人叫你赶紧去呢!”
我立即向梨映院赶去,到了后才发现事情和清然描述得有些出入。
武夫人正和一名男子站在门前,那男子一身绛紫色锦袍,黑发以玉冠束起,面容俊美,神色淡漠,一眼看去竟叫人有些移不开视线。他左手拿着一盏琉璃杯,右手缓缓地抚着杯沿,姿态优雅,贵气十足。他身后站着一人,正是方才向我问路的那名女子。
阁里武功较好的护卫们都站在一旁,中间则有两名大汉正和展离打斗,且照现在的情形来看,展离已经招架不住,不一会儿便会落败。
那两名大汉也眼熟得很,仔细一看,竟是那日我在酒楼前见过的那两人。
武夫人见到我后眼中一喜,立刻对身旁的男子笑说:“周公子,你这边两个人,不介意我也叫个人来帮帮展离吧?”
周公子闻言,淡淡扫了我一眼,轻轻颔首。
他现在这副模样仍是绝美,但身姿修长,英气十足,哪里还有那日我误闯时见到的柔媚动人。
武夫人见状大喜:“花开,还不上去帮帮展离!”
我点头,立刻上前加入战局。那两名大汉并不将我放在眼里,在我接二连三打断他们后,其中一人放弃了对展离的攻势,专注地对付起了我,只是不多久后,那人便被我捏住手腕,轻松的一个铲脚、过肩摔摔到了地上。
和展离打斗的大汉停了下来,用一种十分奇异的眼神看着我,被我摔到地上的那个则动作缓慢地起身,脸上有些难堪,更多的却是震惊。
“好!”武夫人却率先出声,颇有些得意地对周公子说,“周公子,我就说阁里有比你护卫还厉害的人物吧?”
周公子缓缓地扫了那两名大汉一眼,继而定定地看着我。
“夫人,”他黑眸深邃,看不出喜怒,“我要她。”
话音刚落,方才被我摔到地上的那名大汉立刻脱口说:“主子,她可是个……”
周公子淡淡看他一眼,他便马上住了口,却还是有些不服地看了我几眼。
周公子无视在场的其他人,看向武夫人,问:“夫人可否将这位姑娘割爱于我?”
武夫人思索了会儿,对众人说:“除了花开,其他人都下去吧。”等到院子里只剩下我们几个人后,她才慢悠悠地说,“公子想要花开?”
周公子颔首。
武夫人说:“不瞒公子,花开是我花钱雇来的护卫,白纸黑字契约为证,只签了她两年。”
周公子长眸微眯,叫道:“玉珑。”
他身后的女子立刻上前,从袖中拿出了一个紫色锦袋,递到武夫人面前,柔声说:“夫人,这是我家主子从南洋带来的珍珠,望夫人笑纳。”
武夫人眼睛一亮,嘴里稍稍松口:“其实呢,也不是我不肯放人,毕竟花开武功这么好,待在我这阁里也有些屈才。”
周公子对玉珑使了个眼色,玉珑便将锦袋塞到了武夫人的手中,武夫人也不再推辞,大大方方地收了下来:“我虽和她签了契约,她要去哪里也不是我说了算。如果你真想要她,恐怕还得自己去问。”说罢下巴微抬,示意他来找我。
周公子将手中的杯子递给了玉珑,提步向我走来。他站定在我身前,微微俯身,问:“你叫花开?”
我抬头:“嗯。”
他问:“你可愿意来我手下做事?”
我盯着他的脸许久,心里由衷地感叹,美,实在是美。
“花开?”
“啊?”
他重复了一遍:“我方才问,你可愿意来我手下做事?”
“哦。”我摇了摇头,“不愿。”
他眼底仍是漆黑,似是无底深渊,看不出任何情绪:“为何?”
我只耸肩:“没有为何。”
他又问:“你每月月钱多少?”
“二十两白银。”
“五十两。”他嘴角稍稍勾起,眸底却仍波澜不惊,“我给你每月五十两。”
我有些被吓到,一个月五十两,出手也未免太阔绰了些,当即颇为心动,但一想到这人必定不是什么普通人,便还是拒绝了:“还是不愿。”
他微微侧首,似是疑惑:“不爱银子吗?”
这世上没有不爱钱财的人,我也不例外,但嘴里却说:“钱财乃身外之物。”
我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实在是虚伪得可以。
他蹙眉,思考了一小会儿,突然凑近我耳畔,轻声说:“莫非你想让我跟武夫人说那天的事情?”
我不自禁往后退了一步,和他稍微拉开了点距离:“那天是我鲁莽了,实在抱歉。”不过那日他也不是全无过错,毕竟我记得每个房间里都摆着屏风。
他饶有趣味地看着我,又往前踱了一步,再次贴着我的耳际:“你可知道我家乡有个习俗,若被女子看去了身子,便不管如何都要娶那女子为妻?”
我微微瞪眼,只听说女子被人看去了要嫁人,没听说过男子也有这样地说法:“此话当真?”
“当然是……”他慢条斯理地说,“假的。”
我:“……”
“但你若不跟我走,就难保我不会做其他的事情。”他语气虽淡,却带着威胁,明显不是说笑,“那时候的事情,可就谁都不好说了。”
我心里隐隐犯堵,面上却不动声色,只说:“好。”
他似乎很满意自己的威胁奏效,刚想转身却被我开口叫住。
“如你所说,”我定眸看他,慢吞吞地说,“以后的事情,可就谁都不好说了。”
他有一瞬间的愣住,继而意味深长地说:“既然如此,拭目以待。”
武夫人见我答应了周公子后也不再扭捏,只笑着说:“既然花开愿意跟公子走,那我也乐得成人之美。只是有句话我还是要先放在前头,花开这丫头我喜欢得很,今天因为是公子开的口,而且她自己也愿意跟你走,我才割爱将她给了你,不过以后她若是觉得自己更喜欢风月阁,我随时都欢迎她回来。”说罢冲我眨了眨眼,“你可听明白了?”
我点头:“嗯,明白。”
周公子淡淡地看着她,也点了下头。
她这才微微一笑,对周公子说:“那么,公子请跟我来。”
武夫人和周公子走后,玉珑便走到了我面前,轻声说:“我是玉珑,跟在主子身边三年了,以后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找我。”接着指向身后的两名大汉,介绍说,“至于这两个,方才输给你的是路遥,另一个则是马力,他们跟着爷已经有十年了。”
那路遥明显对我不满,撇过头留了个侧面给我,马力则礼貌地对我点了下头。
我也不介意,说:“我叫花开,沈花开。”
“花开。”玉珑嘴角稍稍弯起,眼神极为和善,“我先替你安排个住处,然后再带你熟悉下这园子。”
我点头,脑中却闪过她早上迷路的场景。
事实证明我的担忧不无道理——半个时辰后,玉珑站在走廊上,细眉轻蹙,狐疑地问我:“花开,这个地方……是不是有些眼熟?”
对于路过同一个走廊口三次而不自知的人,我除了深深的无力之外,再无其他想法: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我们方才已经经过这里三次了。”
她脸颊微红,说:“这样啊,真是不好意思,我对这里还是不大熟悉。”
“既然如此……”她轻咳了几声,有些不好意思地问,“你还记得公子的住处该往哪里走吗?”
我在心底叹了口气,照我看,这不是对院子不熟,而是她完全就是个路痴。
我们到时,周公子正坐在书桌前,修长的身躯微伏,神情专注地在写些什么,不一会儿后才对我说:“过来。”
我过去后才看清他写的是新的契约,只是这张契约上,只简简单单地写了一句话。
那句话是:“主子说什么便是什么。”
他问:“你看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”
有什么不对的地方?
不对的地方大了去了。
他放下手中的笔,问:“怎么?”
我抬眸看他,问:“你若是叫我杀人放火怎么办?”
他闻言轻笑一声,似真似假地说:“放心,这种事情自然有其他人做,还轮不上你。”
我又问了好些问题,他都一一作答,并且挑不出任何毛病。待到我在契约上签字按手印后,周公子才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——周卿言。
我心底颇有些好笑,看来这位新主子不仅长得貌美如花,名字也是相当诗情画意。
“花开……”他将契约放在一旁晾干,懒洋洋地靠在了椅背上,“今年几岁?”
“十六。”
他似笑非笑:“是个姑娘?”
我按捺住心里翻白眼的冲动:“是的。”
他故作惊讶:“是吗?看你方才摔路遥的力道,可真不像一般的姑娘家。”
对此,我恭敬地说:“我虽不如公子这般绝色,但的的确确是个女的。”
他细长的眼眸微眯,盯着我看了一会儿,才缓缓对玉珑说:“你先下去吧,我要沐浴。”
玉珑立刻说:“我这就叫人去准备热水。”
“不必了,”他却摇头,“让花开去准备。”
玉珑一脸惊讶:“花开?”
“怎么?”他极其和蔼地看向我,问,“你不会烧水和提水吗?”
我自认脾气心性都极好,但不知怎么,每次和他说话便有种想动武的冲动,可看在一月五十两的丰厚月钱上……也罢,我忍。
“花开,”从他房里出来后,玉珑便有些欲言又止,“不让我叫人帮你一起……”
我知道她想说什么,摇头拒绝:“没事,烧水提水而已,算不上什么。”
她叹了口气,无奈地说:“你日后相处下来就明白了,其实公子待人是极好的。”
我颇有些不以为意,待人极好?恕我眼拙,还真是看不出来。
半个时辰后,我将最后一桶水倒入了浴桶之中,对一旁正闭目养神的周卿言说:“主子,我先下去了。”
他眼睫微颤,缓缓睁眼:“你要去哪里?”
我一手提着木桶,一手擦了擦额上的汗水:“主子沐浴,我自然要回避。”
他却薄唇轻启,慢条斯理地说:“谁准你下去的?”
我擦汗的动作顿住,心底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果然听到他说:“留下来伺候我沐浴。”
我自然义正词严地拒绝:“主子,男女授受不亲。”
他却似笑非笑地睨着我,说:“反正你也见过我沐浴的样子,不是吗?”
我想我以后的日子大抵不怎么好过,因为这位新主子的心眼似乎有些袖珍。
“怎么?”他单手抵着额头,问,“不愿意?”
我心里有些无奈,和他见面不过三次,他却已经问了我两遍是否“不愿意”。我将木桶搁在了一旁,又出去将房门关上,这才走回他跟前,说:“主子请起身沐浴。”
他慵懒地眯着眼,从榻上起身后张开双臂:“宽衣。”
他比我高上许多,我抬头也只刚到他的下巴,不过解他颈上的扣子倒是绰绰有余。他也十分配合,由着我脱下了外袍后又开始解中衣。在此过程中我一直目不斜视,手也镇定自如,似乎一点都不受他影响,但其实不然。我离他太近,近到我能感觉到他宽厚的胸膛正随着呼吸起伏,以及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茉莉清香。这种香味太过好闻,好闻到我竟隐隐有些晕眩。
我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闻到过这种香味,只不过因为锦瑟的一句“不喜欢”,他身上便再没出现过。
“花开,”周卿言突然低下头,凑到我耳旁,温热的气息毫不客气地落在我脸颊上,“怎么停住了?”
我眨了眨眼,继续着手上的动作:“没事。”
他轻笑一声,不再过问。
等到他身上只剩下一件亵衣时,我停住了手:“主子。”
“嗯?”
“你身上只剩一件亵衣了。”
“然后?”
“脱?”
“脱。”
于是在下山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,我竟然已经是第二次“扒”男子的亵衣了。第一次是那名中毒身亡的青衣男子程令,第二次则是眼前这位新主子周卿言,只不过新主子似乎并不如他面上那般享受我的伺候,在我不小心碰到他胸膛上裸露的肌肤时,他微不可察地颤了下身子。
我心里有个念头缓缓聚成,继而唇角勾起,边仰起头迷恋地看着他,边将手心贴上了他的胸膛。果不其然,他眼中有某种情绪一闪而逝,双手也抬起,正预备将我一把推开。
若我没看错的话那种神情应该叫作……厌恶?
对此,我自然是先下手为强地握住了他的手腕,再学着锦瑟平日里的姿态,娇笑着问:“公子,你长得这般好看,肯定有许多人喜欢上你吧?”
他双手暗暗使力,却依旧无法挣脱,接着黑眸冷下:“放……”
“我想答案是肯定的。”我打断了他的话,自兀自地说,“谁让主子长得这般美若天仙,男女不分呢?”
他脸上浮现了冷戾,哪还有半点暧昧调情的模样。
“瞧瞧这张脸,这皮肤……”我不客气地摸了下他阴沉的脸,“堪比女子娇艳,别说是女子了,怕是男子见了也要动心。”
他薄唇微抿,颇有些风雨欲来的趋势。
“主子长得真是赏心悦目。”我叹了口气,“好看,相当好看。”
他不知想到了什么,腕上不再使力,不怒反笑,问:“是吗?”
我笑了一声,将手收了回来,说:“你根本不必试探于我。”我褪去了脸上的娇笑,恢复了平时的漠然,“你是我见过最美的男子,这点毋庸置疑,但你大可放心,我绝对不会对你有任何非分之想。”
他眸色愈加深沉,低声说:“说下去。”
我抬头看着他的脸,淡淡地说:“只因你再好看,也抵不过我心底那人的模样。”
他再好看,也抵不过记忆中那人低头浅笑的一个眼神。
周卿言没有说话,只眼神复杂地看着我,许久之后才缓缓开口:“出去。”
我转身,也不管他的衣服只被我褪下了一半。
我想我方才的演技是极好的,明明看着他的脸,却依稀透过他在看池郁,并且没让他察觉那只是我曾经的爱恋。
我清楚地知道池郁的一切对于我而言都只是过去,即使现在无法忘掉,终有一天也会随着时间的磨砺而消逝无影。
这世上没有忘不掉、消磨不完的感情,从来没有。
我那新主子此刻的心情想必是十分复杂——想到这个,我的脚步便不自禁轻快了起来。其实我能理解他试探我的缘由,年轻公子,相貌极好,出身不凡,身边自是少不了意图不轨之人,防备心比常人重些也是情有可原。他这般利落地向武夫人要了我,一方面极其看重我这身武功,一方面却又怕我一不小心就会喜欢上他。
很明显,这人要的只是我这身功夫。
其实我本没必要这么快就戳破,大可耍他几天,装出一副迷恋他的样子,好好恶心他一把,末了再告诉他:“放心,我对你没意思,逗你而已。”
于是我深深地觉得自己真是个老实善良厚道之人。
回到房中后我又开始收拾起了东西,其实在这间屋子也只住了一个月,但苦命的是我得再次迁移。我的东西还是一如既往不多,几件衣服,两双鞋子,两个笼子,以及……枕头下的那把匕首。
我坐在床沿,将匕首握在手中,莫名地发起了呆。不知多久后才抚着匕首上一缕又一缕的花纹,心底想,拿这个来削木头定是不错的。
这时门外有人敲门:“花开,在吗?”
原来是清然来为我“送行”。
她刚坐下,门外便又有人说话:“沈姑娘在吗?”
听这声音,似乎是两名大汉中的路遥:“请进。”
门外那人推门进来,正是路遥。我问:“有什么事吗?”
他下巴微抬,说:“我想再和你比试一回。”
我心里明白他是惦记着方才丢了面子,刚想回话便听到清然说:“难不成你是刚才败在花开手下的那人?”
路遥闻言脸色更差:“方才我是估计她是个女子!不然早将她打趴下了!”
“嘁。”清然不屑地说,“打不过就是打不过,找什么借口,还亏得你是个男子汉。”
“你!”路遥嘴拙,只能憋红了一张脸,继而愤愤地转向我,“你!出来!我们再比一回!”
我心里着实无奈:“能不比吗?”
路遥脸色微缓:“放心,我会对你手下留情的,毕竟你是女子。”
我摇了摇头,担忧地说:“要是我下手太重,打伤你了可怎么办?”
他愣了下,回过神后异常恼怒,刚准备动手却被身后的人开口制止。
“路遥,够了。”马力出现在门口,笑着对他说,“小心主子知道。”
路遥哼了一声:“主子知道了又能怎么样,难道主子会因为她是个姑娘就向着她?”
马力无奈地笑笑,对我说:“路遥性子直,口无遮拦,还望沈姑娘多多包涵。”
我回以一笑,心里颇不以为然,难道不是你们两个唱双簧,来警告我别对周卿言存有非分之想?
清然这时走到我身边,用一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说:“花开,你以后的日子恐怕不大好过。”
我又想到周卿言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,心底顿时有些没谱。
我是不是给自己惹上了个大麻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