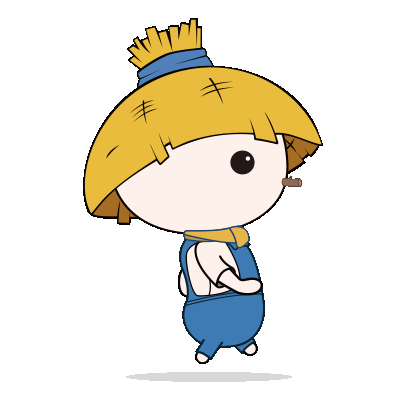“打扰倒是不打扰。”陈平江笑着指了指何治宇脸上的抓痕:“你是被嫂子轰出来了吗?”
何治宇一脸的晦气,讪讪的笑了笑,算是默认了。
在陈平江的印象里,何治宇的老婆秦晗是个挺优雅的女人,后来听说还是东江上层圈子里有头有脸的贵妇,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操作。
“犯了哪条家规呢?”
何治宇双手一摊:“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。”
这时候,刘程笑着搭了一句话:“要我说就把那女的送进去拉倒了,整那么麻烦,天天被人要挟的滋味不好受吧。”
说完这句话后,刘程转头对陈平江解释:“对方是老何公司的一名女员工,本身就动机不纯,想要借机上位,被老何拒绝之后,索要一千万的精神损失费和青春损失费,如果不答应的话,就要将这件事情暴光。老何这人就是心软,下不去手,最后被人小三儿找到了正宫娘娘面前。秦晗别看平时脾气很好,本身是原则性挺强的一个人。”
陈平江听了这话后,想到自己的处境,忍不住心里咯噔一声,顿时心有戚戚。
自己别TM到时候也玩脱了。
心里虽然这么想,嘴巴上依旧嘲笑道:“真不知道你老何怎么混的,区区一千万就难倒你了?当然这也不是一千万的事情,这女的既然有心上位,一千万之后可能还有一个亿。”
所谓男人都会犯的错误,似乎在他们这群有钱有势的男人群体里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儿。
倒也不是没有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存在,但大多数人还是会逢场作戏。
毕竟男人永远喜欢十八岁的,再加上喝酒应酬,难免会堕落有些动机不纯的女人手里。
何治宇自然不是第一个。
见得多了,陈平江早就麻木了。
陈平江认识一个矿老板,离了三四任,现在和第五任也有了小女儿,但是前妻们依旧吃他的喝他的。矿老板也不允许前妻们另找,前妻们自己也不愿意。
一处房产养一个!
更离谱的还有一栋别墅里藏了三个娇,大家彼此接受对方的存在。
“所以,需要我帮什么吗?”陈平江问道。
何治宇连连摆手:“这点小事哪里还用得着你出手,我自己就能解决,只不过念她也曾陪过我,不想把事情做的这么绝而已。可如果她步步紧逼,不识好歹的话,就别别怪我心狠了。今天下午我就会把一千万打进她的账户户头,所有的聊天记录都保存着呢。”
这才是陈平江认识的何治宇,生意能做到这么大的,又有几个是吃素的。
只不过这种事情,陈平江不便发表看法。
总归这些事情传出去好说不好听。
毕竟有吴波怒送小三在前。
陈平江话锋一转,想起了件事:“我看远方广场扩张的速度相当快,你们公司目前的资产负债率是多少?”
“去年的年中报披露的数字是43%,下半年估计又加了几个点吧,毕竟又有几个项目动工。估计全部算下来快50了。”
陈平江皱眉:“有点高了,后面停下扩张脚步,努力降低资产负债率吧。”
何治宇看到陈平江皱眉,没来由的心神晃了晃,他不止一次见识过陈平江那与生俱来的对于市场的敏锐嗅觉。再加上现在陈平江的体量在那,能接触到很多他这个圈子接触不到的消息。
眼下陈平江提出来了,何治宇能不紧张吗?
“现在地产行业狂飙突进,各大集团都在拼命拿地,房价一涨再涨。恒大、碧桂园都是如此,就连老何的竞争对手万达资产负债率都干到了70%,如果远方现在停下脚步,会不会被落下太多?”刘程问道。 陈平江还没说话,倒是何治宇连连摆手:“陈董说降,我肯定就要降。这也是给我个警醒,现在地产实在是太热了,感觉泡沫出现是迟早的事情。这一轮房价涨的夸张,拿地价格也越来越贵。”
陈平江点点头:“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?众人贪婪我恐惧,众人恐惧我贪婪。当然了,这只是我的一点小意见,具体的还看你自己。”
能提醒的就这么多,多余的话陈平江也懒得说。
资产负债率这玩意不是说降就能降的,眼下地产表现的确不错,但一旦寒冬来临,拆不出来钱来,可就要命了。
陈平江脑海里的例子可太多了。
许大老板的事情就不必说了,就连碧桂园后面都只剩下一口气苟活着。
再说万达的老王,东卖西卖,连核心资产都不放过,最后连控股权都丢了,就是为了还债。
有些事情是要提前做准备的,一旦政策收紧,老美加息抽干流动性,资本寒冬接踵而至。
“做生意啊,走的稳比走的快更重要。”陈平江感慨了一句,说出了过年这段时间新得出的感悟。
之前总想着扩张扩张再扩张,殊不知唯有稳健者方能走到彼岸。
做生意比的不是谁厉害,而是谁更长久稳健。
多少昔日里叱咤风云的公司沦落到不堪的境地,数都数不完。
都不需要拿恒大做例子,就单说雅虎,足以说明一切。
看着皱紧眉头的何治宇,陈平江笑着道:“走吧,出去按个脚,今天我请客。这个年憋在家里快闷死了。”
陈平江哪怕已经这么有钱了,对赌钱始终没什么兴趣。
别说澳门了,连朋友之间的麻将都不打。
不赌,这是陈平江自认为数不多的优点。
何治宇情绪调整的很快,心里已经有了警醒,打算年后上班就要着手相关的工作。
听到陈平江的提议,何治宇也来了兴致,陈平江很少提这种建议,他觉着今天一定要陪好了。
打电话联系了一家高端私人会所后,几人一同上了车。
车上,何治宇开起了玩笑:“之前听到个段子,说的是技师的。”
“什么段子,说来听听。”
“你洗的是行走在世间的污浊和泥泞,捏走的是时间磨平的棱角和不幸。
起初我以为今天是一个平淡的夜晚,直到她拎着箱子站在我面前,如同山间的清泉温养的一朵花。
对你来说是洗一次脚,但对于她来说可能是一张过年返乡的车票,是严冬御寒的羽绒服,绝症的妈妈、跑路的爸爸、上学的弟弟和破碎的她。
爱意随钟起,钟止意难平,渐有离别意,加钟抚忧伤。”
陈平江:“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