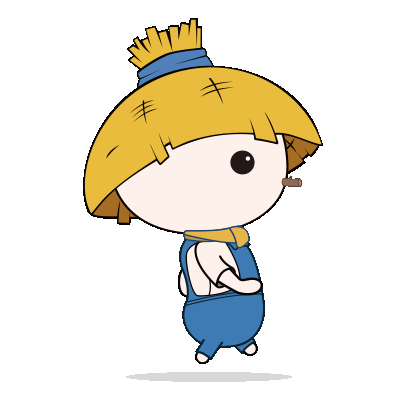葬礼结束后,姜莘怜没有久留,很快便离开。
她最近应该很忙,姜轩斌留下的大笔遗产需要她亲自清点。
季久许回到自己的别墅,并不着急换下长袍,慢条斯理去到厨房接了杯清水,随后踱步到窗前,低头查看百合的状态。
枝干有力,叶片青嫩,不见之前蔫哒哒的病样,一派生机。
他给百合浇了水,将被冲得东倒西歪的小木牌摆正,看着木牌上莘百合的字样,伸出的手顿住。
女人的面容蓦然浮现,浅浅含笑的唇角带着调情的意味,幽绿的眼眸却冷得像冰。
她是口是心非的一把好手,可以娇笑地说出甜蜜的爱语,心里有条伺机而动的毒蛇。
季久许回到客厅,俯身将水杯放在茶几上,挂在脖颈间的十字架随着倾身的动作在空中晃荡。
他握住十字架,举到面前,仔细观察。
是再朴素不过的十字造型,银色的身体没有一点花哨的纹路,只有他掌心那么大,周边消磨得很平整。
和他原先戴着的一模一样,但不是他的。
在姜莘怜伸手搂住他,依偎在他胸膛,她灵活的手指就换走了钥匙。
这把被他做成十字造型的钥匙,能打开教堂里大部分的房间。
他没有与任何人说过,但有机会知道这把钥匙的只有姜莘怜,在她被关进教堂的忏悔室的时候。
正如她自己说的那样,她的手指很灵活,如果换一个人,大概是不会被发现。
但就算发现了,又能怎么样呢?
季久许在沙发上坐下,双腿交叠,侧着头定定地看着手中的十字架,神色不明。
去育儿园传教的时候,他见到了姜钜和园长,预见了他们死亡的结局。
姜钜抢救无效死亡,园长被家族责问关进教堂的忏悔室赎罪,然后被一刀捅死。
同样,他也可以预见姜莘怜的未来。
六亲缘浅,多灾多难,天生薄命。
年幼时被父母遗弃,童年时期被园长打骂,长大一些了被高层选为利益的交换物,再长大些有了保护自己的能力,又在权利的争斗中彻底毁坏了身体。
姜莘怜是个恶人,她的手上沾了鲜血,所以命运惩罚她生来就要受苦,想要的永远都不能称心如意。
她会在几个月后病死,活不到22岁,包括她身边的那些人,也都会死在她的前面。
即将凋零的花,谁会去为难她呢?
季久许知道她的动作,知道她偷梁换柱拿走了钥匙,可他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做,没有揭露她,没有推开她。
以一个不算相拥的姿态,他感受着脖颈间传来的细微扯动,闻到了名为姜莘怜的香气。
如果痛苦在先,那恶人能不能得到一点原谅。
如果真的有神明,祂会将祂的仁慈给予这样的恶人吗?
思绪中断,季久许怔了下,轻声道:
“我开始思考这种事情了。”
【是的主人,你在……】
001也为此惊讶,它思考了一下,措辞道:【你在犹豫】
主人完成了很多任务,积分反馈的力量让他能比肩神明,强大带来了沟壑和距离,逐渐地,他不再像一个人类。
而现在,他和人类一样在犹豫,犹豫要不要插手。
001严肃道:【主人,容我提醒一句,每个世界剧情可以被改变,但唯独人设不可以。
姜莘怜的经历造就了她的性格和未来,早死是她的结局也是她的人设,这是绝对不可以改动的!】
就像不能让已经死去的人复活,命运就是这样不容质疑。
【改变命运不能依靠旁人,只能靠她自己,主人,你应该也很清楚】
虽然季久许没什么表情,看着也不像被冲昏脑子的模样,但001就是看得心惊肉跳,苦口婆心地劝着。
至于后半句,它咽了回去。
神也能改变命运,用以一换一的代价。
*
提到她的过往,总是有人用怜悯的目光看着她,就像姜楚羽。
“一定很痛苦吧”
很遗憾,并没有。
她生来情绪浅淡,痛苦这种情绪自然不会出现在她身上,只是小时候的经历像被蚊子咬了一口,现在有机会了,她要亲自拍死那只蚊子。
“呼,呼,救,救……”
全黑的忏悔室和家族的禁闭室没有区别,园长习惯了将年幼的孩子关进禁闭室惩罚,可轮到自己,仅仅几天就濒临崩溃。
他毫无反抗之力,像只被割开喉咙的鸡,眼睛瞪大,垂死地扑腾。
姜莘怜踢了踢他的身体,确认他活不了多久后,露出一个浅浅的笑: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拖到今天才来吗?”
一刀捅死什么的也太让人不愉快了,他最喜欢的禁闭室惩罚,不该自己亲自感受一下吗?
看着他挣扎的动作停止,没了声息,姜莘怜也不再多留,转身离开。
钥匙插入锁孔,“咔哒”一声上锁了。
事情办完了,这个钥匙该怎么还回去呢?
姜莘怜蹙眉想了想,细眉很快舒展开。
算了,原本还想拉他下水,但是还回去好麻烦,随便找个地方丢掉吧。
她脚步轻快地走出教堂,刚一踏出门,就被大雨拦住了。
这场毫无征兆的大雨下得突然,豆大的雨点密集不断,砸在地面上溅起水花,地面已经积了一层雨水。
这样磅礴的大雨能够冲刷掉所有痕迹,倒是幸运了她。
姜莘怜带好帽子裹紧衣服正要冲进雨幕时,脚步一顿。
豆大的雨珠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细变小,很快磅礴的大雨变成了细细的雨丝,融入地面还积累的一层未来及流走的雨水中。
姜莘怜歪头看着这一幕,比起不用被淋成落汤鸡的惊喜,她倒是有些惊疑不定。
这么幸运的事也会被她碰上?还是说幸运了这一回,马上她就死期将至重病不起了?
好运得像个阴谋。
她思索了片刻,将这些封建迷信丢出大脑,随手将钥匙扔进门口的花坛中,然后快步冲了出去。
银色十字架落在湿润的土壤上没有发出一丝声响,花草将它掩盖得严严实实。
不知道过去了多久,细雨又有了变大的趋势。
穿着黑色紧身衣的男人站在花坛前,修长干净的手指拨开花草,没有寻找的动作,径直捡起了钥匙。
雨水打湿了发丝,湿漉漉的垂在额前,挡住了那双金色的眼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