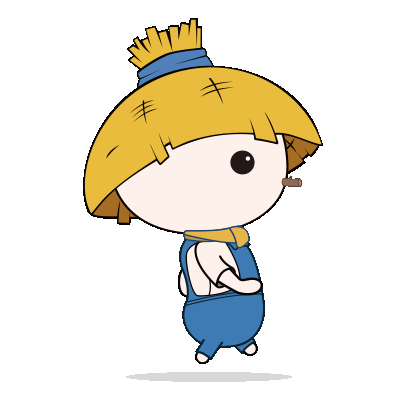多年后,作为一名已经在王都维恩港小有名气的侦探,面对一位风尘仆仆、来自黒木市的年轻委托人,艾苏恩-希茨菲尔不禁又回想起了自己死而复生的那个下午。dasuanwang.
那个时候她还不叫这个名字,她叫冷晴。实际作为冷晴的记忆只有从记事起至十六岁左右。
那时她还是一个男孩,身体里有四分之一的外族血统,在一次暑假被佣人带去国外亲戚的庄园避暑玩耍。
至于为什么不是父母……从她记事以来就从未见过父母的样子。她只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个混血白人,名叫曼苏拉-希茨菲尔。父亲则连姓名都没留下来,自从她记事起就一直是仆人沃菲阿姨在照顾她的饮食起居,包括在每学期参加国内学校的家长会。
所以理所当然的,她国外的那些亲戚们多数也是“希茨菲尔”,一个在她看来半英不英,半德不德的奇怪姓氏。
希茨菲尔家族在当地是大族。但冷晴从未听说过他们的“事迹”。他们住的离城区很远,下飞机后坐车要行驶快三个小时才能抵达那栋庄园。庄园——说是这样说,但实际上以那座房子的恢弘规模称作城堡也不为过。她的英语那时已经很流利了,可以毫无障碍的和那些拥有稀奇古怪名字的亲戚交流。那些人对她都非常的好,包括自称是她曾祖母的卡德珊-希茨菲尔婆婆和自称是她婶婶的阿尼拉-希茨菲尔婶婶。这些人还告诉她她同样拥有一个与之类似的名字,叫“艾苏恩-希茨菲尔”,在庄园生活的日子里他们一直都用“艾苏恩”或是“艾尼”来称呼她。
一切似乎都是很愉快的,唯独有一点:不允许她和其他的孩子靠近后院。
一栋可以用城堡来形容的庄园宅邸,它的后院自然也小不到哪里去。冷晴至今还记得:走一座三米长的木桥穿过溪流来到对岸,入目所及是大片大片疯狂生长的树木、枝叶、茂盛野草,各种她叫不出名字的花卉植物混在其中,一层带花纹的铁栅栏围墙就在这些东西里若隐若现。
一同若隐若现的还有围墙后被称为后院的建筑,那是一栋标准的“洋馆”。一脉相承的建筑风格,精美华丽又不失庄重。她和大部分处于这个年纪的人一样经受不住好奇心的诱惑,偷偷趁一次机会和小伙伴拿了后院大门的钥匙,翻过铁栅栏,开启房门溜进屋内,看到里面的建筑格局类似一个缩小版的教堂。
但和教堂又不一样。
在最前端的高台下方,地上用一种暗红色的颜料画着一个巨大的五芒星,五芒星每条线的内角画着看不懂的暗色符文,四周是一堆堆已经熄灭、长短不一、底座被烧化的蜡粘连在一起的蜡烛,五芒星的正中间是一座供奉式的高台,四周两列共六根承重柱连着六道锁链缠绕在高台上,转头张望,每一根承重柱上都雕刻着不同形态的赤身女神像。
这种类似祭祀、或者某种封印的场景叫其他男孩子吓破了胆。他们停在五芒星的范围之外不敢上前一步,只有冷晴——她记得,只有他选择了继续往前走,来到高台前,嘎吱嘎吱的拖过旁边的一张长椅摆在下面,踩上去,踮脚,将高台上的东西拿了下来。
仔细看,那是一只比她的手掌还大些的木匣。
午后的阳光穿过五彩斑斓的百叶窗投射在木匣上,她看到它是深黑色的,但在反光时能清晰瞥见一层又一层的精美木纹。
那一瞬间,她听到那些同伴们都在对她大喊大叫。
他们说“不!艾苏恩!将它放回去!或是丢掉!”
她也想这么做。
但是她的耳边突然响起了一阵混乱的低语。
无止境、无规律……犹如一万个声音交叠在一起,操着各种语言,用不同的音调,语气在对她咆哮:打开它……打开它!
她重新找回了自我,但匣子已经被打开了。
里面摆放着一颗眼球。
那是一颗非常新鲜的眼球,那种水润的质感,鲜活灵动的神态,以及眼球后方拖拉出来的暗、白交织的神经血丝,这些无一不在向她炫耀:好似它是刚刚被从某具身体里摘下来的。
她和它对视,注意到它的眼瞳是非常漂亮的渐变暗金色。
她盯着那片梦幻般的色彩,渐渐一头从椅子上栽了下来,意识陷入一片无边黑暗。
当她再次醒来的时候,她发现世界已经不一样了。
……
“希茨菲尔小姐。”
“希茨菲尔小姐。”
大脑很沉,连带思维运转都有些凝滞。冷晴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,顿时被一阵强光刺激的又赶紧闭上。
这感觉……就好像有人拿强光手电筒在照她的眼睛。
而且“希茨菲尔小姐”是怎么回事?
就算他和希茨菲尔家族是有血脉上的联系,将来真要选择移居国外,他们对他的称呼不是应该为“希茨菲尔先生”吗?嗯?
“稳住,希茨菲尔小姐。”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。
冷晴感觉有一只手捏住了自己的下巴,强迫他扭头正对强光。
“看着它,看着它,然后告诉我,这是几?几根手指?”
冷晴费力的半眯着眼,依稀看到眼前有人影在不断晃动。他竭力按照对方说的去辨识画面,看到的却只是一个收拢的拳头。
“……一根也没有。”
他回答道。
似乎是太久太久没有开口说话,又似乎是太久没有饮水进食,他感觉自己的声音沙哑变形的都认不出来。
比印象中的声音要尖细了太多,有些像他刚刚进入变声期换嗓的声线,但似乎又比那种声线好听的多。
“很好。”强光离开了。
“没有问题,夫人,这位小姐的意识非常清晰,同时她的瞳孔对光的反应也很正常,应该不是什么邪祟诡异。”
“如果是那样就太好了。谢谢你,格里曼医生。”
房间里响起了第三个人的声音,它明显来自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妇人,声调沉稳,语气肃穆,听上去就给人一种循规蹈矩的教条感。
这个声音的主人怕是不怎么好相处……
声音稍微拉开了距离,伴随房门关闭的声音,周围终于安静了下来。
冷晴大脑里的晕眩感终于也稍稍褪去了些。
他挣扎着睁开眼,适应了一会,驱动身体半坐起来。
意识恢复清醒带来了更多的疑惑。
首先,这里是哪?
为什么,刚才那人会喊我希茨菲尔“小姐”?
本能的,冷晴觉得他可能已经不在希茨菲尔庄园了。
刚想用恢复的视力看向四周,他却注意到了身体的异样。
在坐起身体的过程中,有部分柔柔滑滑的类似丝絮的物体在不断挠他的脸。他伸手捞起一缕拿到眼前,没怎么用力,头皮却已感觉到拉扯的疼痛。
这是……头发?
惊讶的瞪眼,冷晴盯着这缕东西愣愣出神。
不是白色,也不是银色,看起来稍微有些枯槁,像是灰色,那种纯粹由营养不良而导致的参差不齐的灰。
好吧,先不管这异常的发色,就光他突然长了长头发这个问题,以及结合刚才那位“格里曼医生”对他的称呼,他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低头,他看到了两座山包。
不是特别大,远远不到沃菲阿姨那种爆棚的程度。
但也绝对不小,以他对自己的年龄——大约16、7岁这个阶段的认知而言,称得上是发育超前。
它们被一圈浅棕色、针脚细致的布锦包着,外围绣着一层白色的蕾丝花边。再往下是呈双层交叠的浅棕色裙摆,裙摆最前方是一双裹在白色丝织袜子里的秀气小脚。
“……”这绝不是冷晴认知中的自己的身体。
他有些慌张的侧过身体,在床榻下方看到了一双可以称之为可爱的深黑色的圆头皮鞋——但这显然不是关注一个“猛男”应不应该穿这种鞋子的时候,他只胡乱将脚塞进鞋子,目光在房间里四处张望,略过那些典雅古朴的长桌、椅子、钢琴、座钟,迅速冲到一栋衣柜跟前,正面对着它镶嵌上的那面镜子。
他的呼吸几乎停滞了。
镜子里映照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年轻非常有特点的女孩。
她有一头捎带卷曲的银灰头发,长度刚刚及肩。穿着一身浅棕色、带深蓝花纹、黑色线条、纯白花边的有些繁琐的连身长裙。
裙子的领口开的很保守,但依然将她突出的锁骨露在外面。裙摆的长度只没过她小腿的大半,依稀能看到那双愚蠢的皮鞋和白丝脚踝。
脖子上戴着一只黑色的皮圈,黑色与雪白的肌肤形成鲜明对比,让女孩冰冷的气质中混入了一丝丝象征禁忌的魅惑感。
收腰拉的非常紧,显得女孩的腰肢盈盈一握。他本以为这样的收腰放在自己身上会卡的他喘不过气来,但实际上他好像没有什么不畅的体感。
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张和他原本的相貌有些相似,但却已经大变样了的柔和脸蛋。
睫毛很长。
眼角的线条更柔,更软。
蓝色的眼睛都比之前大了不少。
嘴唇比之前小了一些。
颜色也比之前浅了一些,是稍显黯淡的浅棕色。
当然,这些是不足以称之为“特别”的。
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——
他伸手摸上了左侧的黑色眼罩。
“这个是……?”
手指隔着眼罩和眼皮按上左眼,稍稍按压,有阵阵刺痛的感觉传来。
一道暗红色的液体从眼罩里流下,如同血泪,在这张白嫩精致的脸蛋上铭刻痕迹。
我……我的一只眼睛瞎了吗?
后退几步,冷晴有些惊惶的用手去抹脸上的血。
这是得了什么病吗?
眼睛离大脑那么近,会影响吗?
疼痛还在持续……我不会因此死掉吧?
对重伤甚至死亡的恐惧超越了性别转换带来的不适感,在这一刻,他发现他远远没有他预想中的那样在意曾经的身体。
因为他比他预想中的更惧怕死亡。
“那里刚刚上过药,3小时内不要用手碰它。”
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猛地转身,冷晴看到了声音的主人。
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,深棕色的头发大半挽起来束在脑后。一袭收腰黑色长裙,裙摆足足没过脚踝。
目光落在她的胸口,冷晴注意到她还佩戴着一条银色项链,挂坠是一颗类似向日葵一样的圆盘状物体。
“艾苏恩-希茨菲尔。”
她突然开口,继续用她之前听到的那种很庄重很肃穆的声线说道。
“什么?”冷晴一愣。
“艾苏恩-希茨菲尔。”对方重复一遍,“这是你的名字吗。”
“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?”
冷晴没有立刻回答她的问题。
她对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还抱有一定的警惕。
“因为它就在你的墓碑上刻着。”
妇人的回答叫她大吃一惊。
“你是说墓碑?”
“是的。”
“谁的墓碑?”
“当然是你的墓碑。”
“这不可能……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?这里是哪?你是谁?”
“这里是格列家的祖宅,我是格列夫人,一个普通的殡葬师。”
“殡葬师?”
冷晴轻声重复了一遍。
殡葬师,就是那种负责给死人送葬的职业吧。
怪不得她的穿着和语气会这么肃穆,身上也环绕着一股让人不快的死寂气息。
“今天是斋月的最后一天。”
格列夫人依然用那种让人不快的视线盯着她道,“我惯例前往那栋废弃的庄园,为那里的墓碑清扫落叶,恰好听到有极其微弱的碰撞声。”
“碰撞声是指——”
“我循着声音找到地方,那是一块墓碑,上面刻着‘艾苏恩-希茨菲尔,1926-1943’。”
“声音从坟墓正上方的大理石板下传来,我用携带的工具挖开石板,从一具封闭的棺木中找到了你。”
“……”沉默。
“所以那应该是你突兀醒来,但在地下缺少氧气的环境奋力挣扎所发出的动静。也多亏了你本能的挣扎,我才能发现你,救出你,把你带回……”
“等等。”
冷晴打断她,深吸一口气道:“你不觉得这个故事太荒谬了吗?”
假如她死了,她是怎么做到能在地下那种环境一直沉睡到现在还能醒过来的?
这算什么,死而复生吗?
而且这种听上去如此不科学的情况,她在描述的时候语气居然这么平淡。
如果她没记错,她生活的时代分明是两千年后的新世纪了。
结果她死了,在未来复活苏醒,她的出生日期和死亡时间却大大提前了?
除非这里是异世界。
那怎么她还提到了“那座废弃的庄园”呢……
难道那栋庄园和连带的墓地跟她一起穿越了吗。
她当时打开匣子后,到底……发生了什么?
可能是她刚刚苏醒身体还很虚弱,又或许是左眼的伤势带来的影响,越是思维高速运转,她左眼的刺痛就越是剧烈,连带牵扯的整个脑袋都在阵痛,连站立都快要维持不住。
快要摔倒的时候,她感觉有人搂住了自己。
“沉睡了那么久,你很虚弱。”
声音仿佛是从天边传来。
她想说话,但做不到。
疼痛愈演愈烈,她感到熟悉的黑暗在向她逼近。
“再睡一觉吧,艾苏恩-希茨菲尔。”
她听到格列夫人在对她低语。
“这一次,我保证它不会那么久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