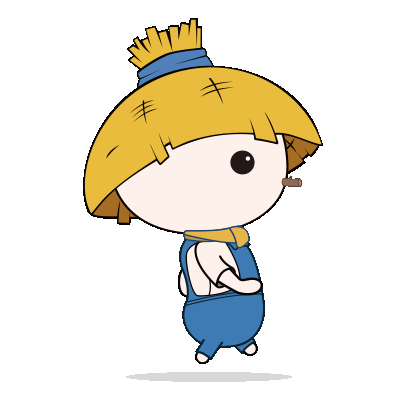宫门戌时前下钥,苏晏掏出西洋怀表一看,刚刚好七点。
左右赶不上,他只能在东宫借宿一晚,不过坚决拒绝了太子想同殿而寝的无理要求,打算去旁边的侧殿。
太子倒是没再强求,而是捧着自己红布似的脸,盘腿坐在罗汉榻上再三回味,不时嘿嘿笑两声。
苏晏羞恼又鄙夷地斜了他一眼,走了。
皇宫外,内城黄华坊的苏府,荆红追和小北、小京守着满桌酒菜等了一个时辰,等来个传话的内侍,说苏大人在东宫留宿,不回来过夜了。
苏小京噘起了嘴:“又留宿东宫啊。咱家大人究竟有多入小爷的眼,老不放他回府睡觉。出京前那一两个月吧,好容易不用进宫当差了,结果小爷直接杀到家里找人,可吓死我!”
苏小北瞪他:“还好意思说!那夜要不是你秃噜嘴,把太子引去了大人的外宅,幸亏没惹出什么祸事,否则就算大人不扒你的皮,我也要狠狠抽你一顿。”
外宅?荆红追瞳孔猛地一缩,手掌不自觉地攥紧剑柄。苏大人养了外宅?是谁,男的女的,他如何不知?
……不知道也正常。苏大人是养外室还是娶妻,有必要知会他一声?不过是个侍卫。开玩笑的一声“小妾”而已,还真把自己当大人的家眷了?荆红追嘴角紧抿。
苏小京很是汗颜:“北哥你就别说了!伴君如伴虎,我知道。以后再不敢在小爷面前胡乱说话。”
荆红追蓦然起身道:“你们两人吃,我去练剑。”
“追哥,吃完饭再练剑也不迟。”苏小北叫住他。
苏小京附和:“对啊,你不饿么?我都饿扁了。”
“不饿。”荆红追说完,持剑走出花厅,来到后院积雪的空地上。
缓缓拔出大人赠与他的剑,上面黑白交织的纹路,在月光雪色下仿佛流动不息。荆红追手抚剑锋,低声吐出两个字:“誓约――”
剑光陡然划破雪夜,寒芒四射,宛如炸开一团飘渺的星云。
荆红追练了一整夜的剑。
-
河汉寒芒飘渺,星影仿佛近在头,“你只是快要枯萎了,但还有得救。”
阿勒坦心底涌起强烈的求生意志,恳求道:“老巫救我……”
老萨满伸长了鼓槌,用骨轮的那一端拨开他的衣袍,暴露出腹部的神树刺青。原本黛黑的刺青,部分枝杈曾被苏晏的血液染成褐红色,如今这红色已淡得几乎看不清。
“等血色完全消失,而你还没来到这里,就救不活了。你是个幸运的孩子,这神树刺青就是你的保命符。”
老萨满说着,挪到几步外的一个石臼边上,往里面放了一捧拳头大的黑褐色果实,开始用石杵用力捣。
“是族里的长老,帮我刺的。”阿勒坦吃力地说,“他说这刺青,会保护我,不受邪锋恶疾的伤害。”
老萨满从石臼里挑起一丝黑褐色的黏液,说道:“刺青的染料里,加了这个,能解各种毒。毒太奇烈,一时解不了的,也能短时吊住你的命,直到你及时找到神树所在。”
“感谢神树,感谢萨满。老巫,你有没有看见我的同伴,送我来这里的那些人?”
“只有一个。”
“他人呢?”
“冻死了。可惜,就差一点,我救不了他。”老萨满掀开布条,给阿勒坦看他的下.身。
他没有下.身,从大腿处被齐根截断,把自己固定在一块装着滚轮的木板上,只能滑动一段距离。
阿勒坦沉默了。他感到一股深深的悲伤,在心底为同伴哀悼,为老巫祈祷。
老萨满仿佛早已习惯,并未流露任何伤感的神情,而是继续用尽全力捣药,咄咄咄地捣个不停。良久后,他拔掉石臼底部的孔塞,将汁液引流出来,盛在一个头骨碗里。
他用一种异常严肃的语调对阿勒坦说:“你得想清楚。”
“想清楚什么……”
“为了祛除你身上的余毒,我要用神树果实捣出的汁液涂遍你的全身。然后你会陷入假死,像冬眠的蛹。”
“假死?我会睡多久?”
“看你身体恢复的速度,也许两三个月,也许两三年。”
阿勒坦愕然,“我……不会饿死?”
老萨满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:“你的心跳会变得很慢,身体里的血流就像平缓的草原河,你可以一连几天都不吃东西……当然,期间我也会喂你一点树果和肉汤。但我老了,记性不好,得等我记起来的时候。希望你熬得住。”
阿勒坦苦笑:“熬不住也得熬。如果不这样,毒性很快就会发作。我能感觉到脏腑间的火还在烧。”
“我让你想清楚的,还不止这个。”老萨满用鼓槌敲了敲他的心口,“你可能会变成另一个人。”
“――什么?”
“神树果实的药性会解你的毒,也会改变你的性情。一个勇敢的人,或许会变得懦弱,一个正直的人,或许会变得卑劣,一个温和的人,或许会变得暴虐――你能接受这样的风险吗?”
阿勒坦张了张嘴,没有回答。
老萨满摇摇头,“我知道,这很难。”
他用鼓槌敲起抓鼓,曼声唱起了另一首神歌:“召唤自我之魂灵,呼来,呼来,呼来。愿所求福吉都能实现,如所向往……”
阿勒坦沉默着,考虑着,是作为自己死去,还是作为另一个人活着。
“我……”他犹豫道,“所谓风险,也不是必定,对吧?”
老萨满从长吟转入短促的鼓点,没有回答。砰砰的鼓声,像紧张的心跳一样催促着他。
阿勒坦并没有犹豫太久,就下定了决心:“想猎杀野狼,就得冒被狼牙咬穿的风险。想捕捉鹰隼,就得冒被爪喙撕裂的风险。想从绝境中求得生存,哪可能不需要冒险呢?老巫,我愿意接受。而且我相信,无论再怎么改变,我阿勒坦还是阿勒坦!”
老萨满敲下最后一个沉重的鼓点,再次露出难看的笑容。
“还不止。你的刺青渗入了另一个人的血。我想,给你刺青的人,应该告诫过你。”
阿勒坦回忆道:“是的,不能让其他人触碰这刺青,除了父母和……伴侣。”
“所以那个人必须成为你的伴侣。在你复苏之后的三年内,如果没有得到那人的身心,没有双双跪在神树面前许愿结合,你会遭受刺青的反噬。
“那人的血,会变成你致命的毒,无解的毒。
“你会死。”
阿勒坦震惊地睁大了眼睛。他慢慢抬起手臂,上面缠绕着一条淡青色发带。经历一路风雪尘土,发带早已变得灰扑扑,末端的叶形玉坠也掉得只余下最后一片。
苏晏……会同意吗?在他醒来后的三年内,他们能否重逢?面对很可能性情大变的北漠王子,身为大铭官员的苏晏,会愿意和他身心交融,结为一对吗?
这太遥不可及了!比在药力下牢牢守住自己的性情还要难……
阿勒坦不自觉地摇着头,努力回想那个中原少年的一颦一笑,希望从中捕捉到丝毫对自己的另眼相看。
但他十分遗憾地发现,相比他对苏晏生出的浓烈好感,苏晏对他似乎连好感都称不上,只当是个萍水相逢的、还算投缘的朋友。而这“朋友”二字,还是在与国无害的前提下。
他始终记得,苏晏那句饱含警告的玩笑:
“如今瓦剌连一个贩马的青年,都能吟诵描写我国京城的诗词,贵部该不会也有叩阙之念吧?”
当时他想说,我对大铭只有向往,并无侵略之心。但话到嘴边,却又咽了回去――真是如此么?除了仰慕,就没有一点想要占有的野心?
阿勒坦长长地吐了口气。
老萨满问:“想清楚了?”
阿勒坦点头:“我想活下去,哪怕不知道能活多久。或许三年后就是我的死期,但至少我努力过,争取过。胡杨尚且扎根于沙漠,雄鹰尚且筑巢于悬崖,而我堂堂一个男子汉,怎么能不战而退!”
老萨满点点头,把手伸进头骨碗,舀起一�黑褐色的半固体药膏,涂在了他腹部的刺青上,随后向上下抹开。
这一碗药膏用完后,他又捣了三次,才堪堪涂满阿勒坦的全身。
阿勒坦身无寸缕,被逐渐干硬的药膏裹成个泥人。老萨满脱光他的衣袍,摘除他身上所有的黄金饰物后,想要继续摘除他手臂上缠绕的发带,但阿勒坦坚持要留着。
“你胳膊上会出现几圈不同于其他皮肤的颜色,像蜕皮的蛇,很难看。”老萨满提醒他。
阿勒坦不介意,“我不在乎,我要留着它。”
既然他这么说,老萨满也不再劝,一边击鼓唱神歌,一边看他逐渐丧失了意识。
鼓声忽然又停顿,老萨满挠了挠满是泥垢的耳朵,自言自语:“哦,我真是老了,忘了说,还有个风险――你可能会忘记过去的一些事,一些人。或许也包括送你发带的那个人。”
“唉……”老萨满长叹口气,唱道:“你是地上原野的主宰,长有一万颗坚强的心。”
―――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