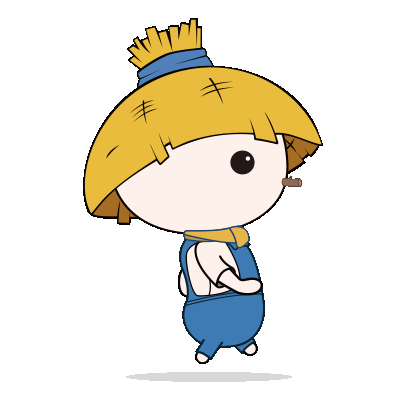夏晚栀工作室是三室一厅的装修户型,一间画室,一间杂物室,另外一间便是陈列室。
陈列室室内很宽敞,防尘布遮挡着每一幅夏晚栀从小大的作品,每一幅作品都按年份整整齐齐地陈列着。
夏晚栀往里走,按照年份编号停在某个区域开始翻找。
七八年前画的画基本上不是很大幅,又大多都是练手的画,所以都是用格拉辛离型纸垫着一幅一幅地从下往上垒起来。
夏晚栀只能一幅一幅地看。
谢祁延站在一侧视线紧紧跟随着夏晚栀寻找的动作,他浑身紧绷着,呼吸沉重到渐渐生出一种复杂的情绪。
期待中藏着害怕。
害怕又是一场梦。
“找到了。”夏晚栀把画抽出来,将一幅长宽五十厘米的油画抽出来。
这是一幅具有梦幻色彩的画,背景是花海与蓝天,但画面的布局很奇怪,能飞的不能飞的物体都统一出现在天上,而地面只有锦簇的花团,每一朵花都是不同的形状和颜色,最突出的是一朵巨大的粉红芍药,芍药上坐着一个小人,笑嘻嘻地望着天。
天上的的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抽象的。
按理说,这更像是一个小孩子的梦。
可梦境这种东西,本就是千奇百怪的。
夏晚栀微微抿唇,她共情能力强,理解那种以为看到了希望到头来却是一场空的感觉有多难受。
“抱歉,凭着一幅画好像不能确定我见到的那个人就是你妈妈。”夏晚栀隐隐觉得愧疚。
当初如果把人画下来就好了。
可惜这幅画记录的是那位阿姨的一个梦。
谢祁延扶着画框,呼吸渐渐变得急促起来,巨大的欣喜充斥在每一个细胞之中,他喉结微动,张了张口,缓缓伸手覆上油画中间的那一只背着一把长剑骑在飞机上,伸展着两米长的手臂在花园上空盘旋着的四不像小男孩。
小男孩挂着火红的披风,腿长两米八,从飞机上直直坠下来就快要接触到地面。
长了翅膀的乌龟,穿着迪迦奥特曼衣服的小狗,还有头顶光圈的小猫,拿着话筒唱歌的面包……
这么幼稚,这么天马行空,这么抽象,这么多的奇思妙想。
“是她。”谢祁延控制着隐隐颤抖的手,视线聚焦在这幅画上,他说,“她姓姚,单名一个琴字。”
“她喜欢芍药,想长在花苞里,当一只精灵。”谢祁延沉着声。
“这是她的梦。”
他隐忍着,却在这一刻没绷住情绪,沙哑着声:“她的梦里都是我。”
骑着飞机上天的抽象小男孩,是他。
小时候跟妈妈在一起的谢祁延很多话,别人家的孩子一两岁说话还磕磕绊绊时,谢祁延就已经拿着小话筒当麦霸了。
他说话早,认字早,会说的词语多,画上的这些内容,是五岁那年过生日时他跟姚琴女士说的奇思妙想。
不是他的梦,是他跟姚琴女士说的每一句富有孩童之气的话。
她记了这么多年。
她心里有他。
可是谢祁延不明白了,她为什么当初狠心将他抛下。
不明白这么多年来,她为什么一次也不来看他。
夏晚栀的心情很复杂。
不仅谢祁延需要消化,她自己也要消化。
她没想到自己冥冥之中跟谢祁延的母亲竟然相处过两天。
“其实我不太记得了,我画了很多别人的梦,接触到的人很多,但是印象里,你妈妈很温柔。”夏晚栀跟谢祁延面对面坐着,垂着眼睫小口小口地喝着一杯茶,有些不适应谢祁延忽然这么直白又强烈的目光。
“当时游客很多,我们只是巧合住在同一个民宿里,两天后她就走了,彼此也没留下联系方式。”夏晚栀抿了抿唇,指着那副天马行空的画说,“这幅画其实还是我认领的,应该是你妈妈落在了民宿哪个地方,被民宿老板捡到挂在失物招领处。”
“我想着毕竟是我呕心沥血画的作品,所以就带回来了……”
夏晚栀完全可以说是忘记了这幅画。
要不是因为谢祁延,这幅画估计还静静地躺在她的陈列柜上。
“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?”谢祁延直直盯着夏晚栀,激动的心情难以掩盖。
夏晚栀挠了挠脖子,轻咳:“我都有些忘了,你等我回去找找照片。”
夏晚栀去过的地方太多,脑子又不太记事儿,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,也许还可能落下很多细节没说。
半晌,谢祁延终于将目光从夏晚栀脸上移开。
夏晚栀轻吐了一口气,有些如释重负。
谢祁延简直,缠人得可怕。
颇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气势。
这种气势按理说应该有点凶,可是刚才的谢祁延,模样看起来有些可怜。
“她……长什么模样了?”
谢祁延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向她抛出问题:“身体看着好不好?是不是一个人?”
夏晚栀有问必答,把知道的都说了:“很温柔慈蔼,身体应该不错,我见她时是一个人,但是她不爱笑。”
而谢祁延给她看的那张照片里,她笑得很好看。
这个话题结束,周遭的空气再次凝固,这一回安静了许久,夏晚栀看着陷入沉思的谢祁延,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原来整天冷冰冰的黑面阎罗,内心深处也有自己脆弱的一面。
或许外界的那些传言,都只是片面的,他以前认识的,或许不是真正的谢祁延。
认识一个人,从来都是要靠自己去认识。
“夏晚栀。”谢祁延端坐着,忽然抬眸很认真地跟夏晚栀对视着。
突然被这么严肃地喊名字,夏晚栀眼神游移了一秒,心想自己今天见到他脆弱的一面不说,还知道了关于他内心深处的秘密,这人该不是要杀人灭口吧。
“我……”保证不说出去。
“谢谢你。”谢祁延的话缓缓穿入她耳中。
夏晚栀愣住,把没说完的话咽回肚子里。
“不客气。”她舒了一口气,语气变得温和。
“这幅画,能赠与我么?”谢祁延从拿到这幅画开始就一直未离手。
夏晚栀微微一笑:“本来就是你妈妈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