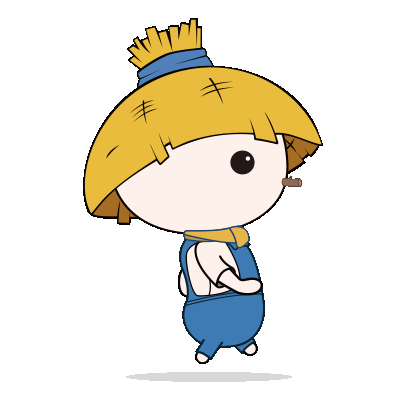李昰刚走,何泌昌便将目光看向了赵诺三人。
“三位,在下何泌昌,表字用修,这厢有礼了。”
看着文质彬彬,躬身作揖的何泌昌。
赵诺二话不说,便直接跪倒在了地上,像是见了青天大老爷般倒起了苦水。
“先生一定要救我们啊!”
他们本以为来这保国观是替大户人家修行。
谁成想是被抓来制铜。
制不出来,还不许吃饭。
之前吃的那顿羊肉泡馍,是他们吃的最后一顿正经饭。
最近没有‘科研’进展,他们日夜只能靠喝粥度日,别说饭了,连盐都没吃多少,走路都觉得两腿发软。
听赵诺倒完了苦水。
何泌昌的眉头也已经皱成了一个‘川’字。
“吴管家,他们说的是真的?”
“是,这都是我们姑爷吩咐的。”
何泌昌听完之后,不住的摇着头,最后斩钉截铁道:“简直胡闹!”
三人眼中同时迸发出了象征希望的光芒。
这四个字,他们已经等了太久了。
终于有人觉得这是胡闹了!
当街抓流民点石成铜,跟逼母猪上树有区别吗?
“青天大老爷,您可一定要为草民做主啊!”
赵诺三人眼中再次噙满泪光。
他们现在真的后悔了,当初就不该占这个便宜。
哪怕是饿死街头,好歹还有个全尸呢,现在稍有不慎,就得崩东一块西一块。
何泌昌箭步上前,抓住吴管家敦敦教诲道:“老吴,不是我说你,学问不是这么做的。”
赵诺三人听得连连点头,像是小鸡啄米。
看看人家!
“明理他天赋异禀,玩着都能考中进士,饿两顿自然可以顿悟。”
“你看这三位哪有明理那样的天赋?”
“做学问,虽不似耕作,但也极耗体力,怎么能捱饿呢?”
听到这里,赵诺三人的表情同时凝固。
直接告诉他们。
这人不对劲。
吴管家已经挠了挠头不解道:“那表少爷的意思是……?”
“好吃好喝好招待,头悬梁,锥刺股就是了。”
“他们也没这么大尿性啊。”
“他们没有,你不会帮他们啊!帮他们悬梁,帮他们刺股,以前在家就是我爹干这活,我这腿现在阴天下雨还疼呢。”
何泌昌挥舞了两下拳头。
吴管家顿时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。
怪不得人家能考功名呢!
左右再次被家丁包围,赵诺险些一口老血吐出来,连忙跪地求饶。
“别,别,我不悬梁,不刺骨。”
“饶命,吴大哥饶命啊!我们真就是来混吃混喝的啊!”
对此,吴管家充耳不闻。
这保国观里什么都有,明晃晃的三把锥子很快便出现在吴管家手中,道场内也再次响起赵诺那鬼哭狼嚎的惨叫声。
看着被锥子架住,上吊绳捆住的赵诺三人,何泌昌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“对嘛,这才有个做学问的样子。”
“咱们这种天资愚笨的,就应该有愚笨的觉悟,我是过来人,当初我考功名的时候就是如此,熬过去就好了!”
“姓吴的,你小子别犯在老子手里!”
“吴管家莫怕,将来学有所成,他们还得谢你呢!”
赵诺一时词穷,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。
考功名跟制铜是一回事吗?
进士再难考,最起码有人考中过啊!
这帮达官显贵里面,还有正常人吗?
何泌昌没有理会惨叫连连的三人,却是将目光看向了面前的丹炉。
“这怎么只有一口炉?”
清风、明月两人愣了下。
“不……不然呢?”
“就一口炉够干嘛的?一人一口!让徐阶知道了以为我们炼不起呢!”
“三人共用一本书怎么能考好?”
在何泌昌的敦促下,每个人都获得了专属炸弹……丹炉。
每人身后,还跟着一个小书吏,负责记录每次炸炉的成分配比。
钱贝红着眼睛,孙尔吸溜着鼻涕看向赵诺。
“哥,快想办法吧,我算是看出来了,再待下去,咱们非死这不可。”
“你们以为我不想跑啊!这帮人跟盯贼一样盯着咱们仨,咋跑?!今晚先吃顿饱饭再说,总能找到机会。”
“干嘛呢?!”
远处倏然响起一声何泌昌的怒喝。
三人不约而同的打了个激灵。
赵诺立马绷直身子,连道:“先生,我们仨讨论学问呢!”
听到赵诺这么说,拎着戒尺的何泌昌才悻悻离去。
好在保国观是天子御赐给陶仲文的府邸,规制相当宏大,除了偶尔传出些爆炸声外,赵诺三人的惨叫声压根就传不到三清殿的香客们那边。
……
胡大顺现在是钦封的‘神霄保国宣教真人’、与张天师同掌道教事。
既然要宣教,时常还要开坛讲座论道,自然就不能躲在清净地,胡大顺的道场就在三清殿旁边,也是供奉陶仲文神龛的地方。
在道场前还有一处高台,周围移栽了不少大树,树荫刚好遮住高台,只不过今日没有宣讲,高台上并没有香客,有些冷清。
李昰眉头一蹙,不解道:“怎么还神秘兮兮?”
刚才在众弟子们的道院,还有时不时能见到人。
现在离正门更近了,按理说没有道童,也应该有些香客,反倒不见半个人影了。
“胡真人?”
“胡大顺!”
李昰满腹狐疑的上前推开道场门扉,一股香烛混着各种药材的味道扑面而来,墙上的浮雕是阴阳太极鱼,地上铺着的是与紫禁城一般无二的金砖。
偌大的道场内,就只有陶仲文的神位、神位下一个空荡荡的蒲团跟左右两排药柜以及两对椅子、茶几,更不见半个人影。
茶几上倒是沏着一盏热茶,显然是给李昰沏的。
“这么大人了,怎么还耍人玩?”
李昰心生不悦当即便欲起身离去。
只不过很快便听到里面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。
秉承着来都来了的精神,李昰探过头去。
却见药柜后面,摆着张书案,书案旁,一个似曾相识的小娘子身穿道袍,手持毫笔,赤着脚趴在太师椅上伏案抄写经文,见李昰过来,遂起身来媚眼如丝道:“官人,久违了。”
那声音直教人骨头发酥。
扬州瘦马腰肢细,西湖船娘臂轻摇,大同婆姨门叠户,泰山姑子善坐莲。
只不过看着这搔首弄姿的小娘子,李昰竟是不由得有些生气。
道德在哪里,尊严在哪里,派她来的人又在哪里?
瞧不起谁呢!
此地无银莫过如是了。
连要办什么事都不敢说,哪个朝廷命官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