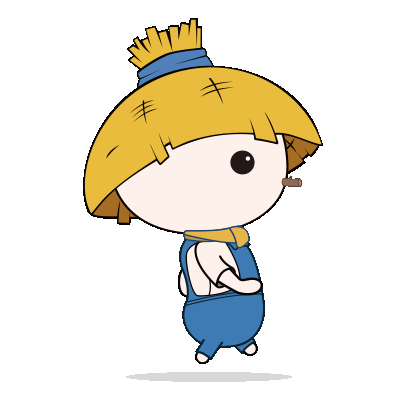洪良玉一路进山到了炭窑,瞧见凉棚下头站着个肥悍妇人,满脸的横肉,身后边杵着个穿破花袄的半大丫头,下巴尖尖的,两腮微陷,许是饿的。
收炭的李三抿了一口凉茶,斜眼瞅着喋喋不休的妇人,半天才不耐烦地摆摆手:“花婆子,你不要白费口舌啦,东主今年已经新娶四房啦,丫头也添了十多个。就她?我可引荐不了。”
他站起来提了提裤腰带,上下打量着这丫头,笑嘻嘻地说:“要是跟我,倒还不错。”
“去去去去。”花婆子一把把李三推开:“那东主娶了我们翠儿,聘礼能给一大车呢,你,就你,你你,你能给多少?”说道最后,花婆子声音矮了一截子。
李三嘬了嘬牙花子,伸了二根手指:“两吊钱。”花婆子听得直翻白眼,李三劝道:“你不吃亏。她在你家待了半年多了,吃了你不少吧?”
看花婆子眼珠乱转,李三趁热打铁:“她家里没别人了是不是?逃难害了痢症?”
花婆子听了急眼了:“土匪!逃难半路上叫土匪杀了,没病!”
“不管怎么死的,这女子你还养得活么?你家里还有两儿子,再说我不是买,明媒正娶不是?咱们街坊这么多年了,我娶过门就是自己的媳妇,亲亲热热还能亏待她?也算你这当表亲的对得起她爹娘了。这是什么年头啊?把姑娘扔到荒坟野地撒手不管,就当扔一条野猫,那大有人在,你有良心啦!”
那悍妇盘算了一阵:“我琢磨琢磨。”说完就把丫头扯到了一边。
洪良玉木着脸走过来,李三见是洪良玉,一下子站起来,倒了杯茶水递上去,堆笑道:“二哥,您来上工了。”
洪良玉初来不久,李三一个收炭管事,居然对他倒十分恭敬。
原来洪良玉没来几天,炭窑突然出了事故,山一般的积碳突然崩裂,十几名取暖的烧炭工连同收炭的管事李三全被压在炭下,是洪良玉赤手空拳把十数名炭工全部从炭下挖出,这才避免了一场惨剧。
洪良玉没有接眼前的茶水,开口道:“李三,咱们都是清苦人出身,你可不能昧了良心,那是条性命,不是猫猫狗狗。”
任谁被洪良玉这猛张飞一般气魄的大汉直勾勾盯着,心里都会发虚。
李三拿手搔了搔后首:“二哥您这话是怎么说的,我这不是……我这小三十了也没媳妇。”
李三咽了口唾沫:“花婆子家里也不富裕,这丫头吃不了几天啦。那回头真……性命不就糟蹋了?诶,二哥你是不是看上她了?那没关系,你一句话,兄弟我……”李三一拍胸脯:“让了。”
“我没那意思。”
洪良玉一瞪眼,他还想再说什么,可话卡在嗓子眼,半天说不出来,看了一眼凉棚外头,花婆子正对着丫头一会儿掐骂,一会儿作揖,演戏似的声泪俱下,这丫头也不哭,木了一会儿,终于点了点头。
洪良玉叹了口气,自己十六岁的时候,家里实在养不了两个孩子,这才投了红旗,这些年刀山火海,九死一生。在船上养伤时,偶尔想着什么时候能不再打打杀杀,回自己的安乐家乡,或者干脆在大屿山颐养天年。
那一天红旗收到消息官府要来围剿,洪良玉本来做好了死战的打算,没想到天保龙头却遣散了所有在两广还有亲故的帮众。洪良玉那时百感交集,本以为天地大宽,怎么现在绑手绑脚,看见什么都不称心呢?
他摇了摇头,没再说什么。
※※※
砰!
厚厚的一筐黑炭摞到地上,洪良玉深吸一口窑外的新鲜空气,缓缓吐出,扑打下身上的炭渣黏土,结束了一天的工作。
身边一名看上去二十出头的壮小伙子一屁股坐到地上,拿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汗,攥紧了手里的几枚铜钱,忍不住问道:“这官府有典制,每黑炭千斤,准银要三两三钱,本料五钱银子,怎么到我们手里,一千斤炭只剩下区区二十文钱呢?”
“错了不是?”
一旁稳坐的老账房拨弄着算珠:“账可不是这么算的,你们挣多少钱,和炭价没关系。”他一指上头:“和天老爷有关系。”
壮小伙疑问:“这怎么讲?”
“这天老爷要是生了气,老百姓遭了灾,连饭都吃不上,就得抢着当炭工,这人多了,东主出的工钱,自然得少。这要是丰年,没人烧炭,你们这钱不就涨上去了?”
账房把算珠打得噼啪作响,最后才一收:“瞎抱怨没用,你要不干,有的是人干。”
洪良玉本不说话,听到这儿才道:“老先生会算账。”
账房头也不抬:“嘿嘿,小子,你甭挖苦我,我告诉你吧,按东主炭窑的规矩。所有新来的炭工,前五千斤炭是不给钱的,只管饭,你这不是洪西宾推荐的人嘛,东主开了金口,给你免了。你呀,别不知道好赖。”
壮小伙直挠头:“好像有点道理,又好像没道理,那我干了这些年,也没见着涨钱,合着天老爷年年生气,他老人家气性也太大了。”
他说得幽默,惹得一身脏土热汗的炭工们哈哈大笑。
“二哥,今天放工,要不到我家去,我丈人前几天来瞧我,给我留了两斤黄酒,咱哥俩近乎近乎。”
“今天不行,我得到唐家庄去一趟,我朋友出了趟远门,家中小妹无人照顾,我寻思把她接来,同我嫂子一起住。”
“诶,二哥是有好心眼,可咱这秀才老爷能同意么?”
洪良玉慨然一笑:“我大哥刀子嘴豆腐心,无非骂我两句。”
也有炭工一听皱起眉头:“唐家庄可不似咱们这儿安乐太平,听说那边闹了灾,路上有土匪,还有人造反,你可要小心啊。”
洪良玉面上木讷,心中却冷笑一声:“造反?我家天保龙头正是造反的祖宗,论起来,我也是他叔父辈了!怕他个鸟来!”